仿真的再現─1980-2004港台恐怖電影的後現代轉折
郭宏昇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後現代被稱為是一種相對於「現代社會」所體現的文化現象。在這種的論述中,找不到所謂的原點,如果這個原點是承載著龐大的敘事意義的話。英國社會學家麥克•費塞斯通(Mike Featherston)就曾經寫道,「說起後現代性,就意味著一個時代的轉變,或者說,它意味著具有自己獨特組織原則的新的社會整體的出現,意味著與現代性的斷裂」(Featherston,2000:4)。現代性作為一種群眾認同的特質描述,和消費文化透過主要的方式連結在一起,首先,個體選擇支配我們社會性感受的隱喻;在自我需求或追求自我下所進行的個體選擇,逐漸成為理解社會行動和結構的方式,透過消費的想像能夠取得對現代認同的絕佳認識(Slater,2003:147)。然而,在類似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提出的「後現代」論點當中,消費文化與電子媒體的誕生是一種使人們去卻人性的武器,也透過「擬像」的再製讓我們無法辨別虛實,進而承認擬像符號本身所創建出來的真實。在這個論點之下,我們可以很明顯的歸納出「後現代」之於標榜著科學理性、進步的「現代性」有什麼樣的「斷裂」:仿真、去中心化(decentering)、符號大於物質生產關係的邏輯、意義複製等等,都是後現代社會的特徵之一。而在我們的生活世界中,我們如何透過感官來確認後現代處境?這個理由促發了本研究動機,並選擇以1980-2004港台恐怖電影為研究對象,利用法國社會學家布希亞所提出的「擬像」四重分析(simulacrum)加以論述(理論部份將於第二章討論),目的不在於批判這些文化現象,也不著重在恐怖片做為消費文化一環的政治經濟學討論,而是透過此一時空脈絡下的電影再現,抽離出華人鬼神觀的後現代轉折及其表現。
長年以來,恐怖電影一直是最受觀眾歡迎,同時也是獲利最多的電影類型之一,細數過去三、四十年的好萊塢影史,很容易發現恐怖片經常是暢銷電影排行榜上的常客(謝旭洲,1999:91)。當然,恐怖片也是商業電影的一環,它通常利用突如其來、快速、震撼式的手法來展現戲劇張力,目的是給予觀眾一種立即的感官刺激,透過驚嚇來傳達娛樂效果,Crane(1994:2)就曾經轉述Carol J. Clover在1992年所說的話:「(恐怖)電影成功的去給予觀眾痛苦(hurting
its viewers),就是好的恐怖;如果不是,那就是劣質的恐怖」。
但是基於電影製產的全球化趨勢,似乎一談到「恐怖電影」,我們自然會想到由好萊塢創造的恐怖明星(如《十三號星期五》裡的Jason
Voorhees、《半夜鬼上床》的Freddy
Krueger),卻忽略了以華語為主的恐怖電影類型也有其發展脈絡,並與我們觀念中對於「鬼」、「恐懼」的認知更為貼近,並且隨著時代轉變,這些再現模式也產生了轉變。
東西方「鬼電影」的一個差別,在於西方的鬼片是種「類型電影」(影響雜誌編輯部,1997:18)。所謂的「類型」(genre)源於法文中「形態」或「種類」的意思,在電影範疇中以一些不同的標準與要素,拿來指涉某個範疇或某個種類的電影(KingZKrzywinska, 2003:3)。好萊塢電影產業所創造出的恐怖明星以及用「恐怖」做為市場區隔的影片類型具有高度的類型學典範,美國就在這樣一種將「恐懼」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的企業經營之下進行創作,目的是使人記住「怪物的形象」,而不是故事脈絡本身。但是基本上,「恐怖片」的分類也不能完全與科幻片(science fiction)、犯罪片(crime film)、冒險奇幻片(adventure
and fantasy film)等類型電影做區分(Neal,2000:92),因為許多引起恐懼的元素也同樣在這些電影中出現,這點在分析港台恐怖電影時也有異曲同工之處(如《人肉叉燒包》系列),所以這裡所指稱的「恐怖電影」,是一種類型學上(typology)的討論,而不是絕然的敘事元素判準。
而相較於好萊塢,華語世界的「鬼片」與「恐怖片」更是模糊的類型分屬。華語恐怖片有來自古代傳說的應用,早期像《倩女幽魂》系列,就是來自聊齋文學傳統的延續,以及源自於中國的鬼神觀;一部份則是通俗劇精神的影響,與電影美學的傳承(聞天祥,
陳儒修曾經對於東西方鬼片的類型差異提到下列一段話(影響雜誌編輯部,1997:18):
……東方鬼片的類型化程度,其實不如西方鬼片來得高,而無論是鬼電影、鬼故事等,它 們都屬於次文化的類型,它反映出的是人類的某種好奇心─人類總是想去預測另外一個未 知世界的形貌,揣想死後世界的形形總總。
在港台的恐怖電影當中,一直引用了與道教有關的符咒、作法等儀式,以相對於鬼物的存在,並提供一種消解恐懼的方式,同樣的,也是一種對死亡(或亡者)的追崇模式。在這個時期,「中國傳統」的驅鬼技術十分明顯的融入在電影裡,「茅山道士」與其「法術」的符號藉由「中國記憶」再現於電影之中,符合布希亞仿真的第一階段:符號反應出基本「真實」。特別的是,以香港為首的華語電影圈,「鬼片」的生產是在1980年追隨著武打功夫片的熱潮演變而來,當時的《鬼打鬼》便為此類型的產物,並掀起一陣跟拍風潮(
本論文觀察到此一現象,便企圖將1980到2004年的港台恐怖片視為研究文本,選了幾部在當時造成熱潮的影片,用以分析透過電影再現出來的華人世界,是如何呈現出「鬼」以及「恐懼」的後現代特徵。本論文目的不在於將港台「鬼片」與「恐怖片」做一種明確的區隔,而是以文化分析的角度去看待這「類型」(姑且將之視為一種可供探討的電影文本)的電影是如何反映出擬像規則。
第二節 研究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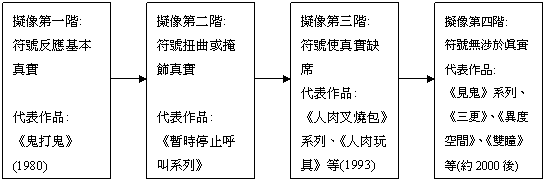
本論文利用布希亞對於「擬像」的後現代分析觀點,抽離出港台恐怖電影在時空轉變中,所呈現的虛實符號,藉以突顯出華人鬼神觀的後現代轉折。基本的文本討論規律如下:
圖一 文本討論規律圖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國內針對港台恐怖片所做的研究與專文、專書十分稀少,大多停留在電影美學討論的層次上,或是由西方引進的電影做為開端,而且恐怖電影本身常被歸類在商業電影的範疇裡,因此除了票房討論幾乎不受重視。國內曾有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林彥甫(1996)所做的碩士論文《觀看恐怖電影的心理機制─以「認同」分析「半夜鬼上床」》,算是國內針對恐怖電影做討論的濫觴,不過仍停留在好萊塢的電影而不是華語恐怖片,而且是以精神分析的角度加以論述,相反的,以後現代觀點、將華語恐怖片系統化整理的文獻仍付之闕如。華語恐怖片的分析相較於歐美是慢了許多,以系統化的著作而言,國內僅有一本由Paul Wells(2003)針對好萊塢恐怖電影進行的翻譯本,算是可以在分析華語恐怖片時具有對照性的參考價值。國內以港台「鬼電影」為主軸的專文除了影響雜誌編輯部(1997)、聞天祥(2000)、
第一節 恐怖電影做為社會實踐的要素
電影不僅是一種藝術形式,更是各種各樣的社會實踐,若把電影放在社會脈絡中來看,可以發現電影往往體現出多重的宗教、文化關係(
在電影理論家梅茲(Christian Metz)的觀點中,觀眾並不是個人(individual),而被視為一種透過電影機構所生產、再現的人為建構(artificial
construct),在某中意義上,電影是透過「虛擬效果」(fiction-effect)來建構其觀眾(林彥甫,1996:19)。有了觀眾將電影傳播出來的影像視為「真實」的前提,才能使電影再現成為可能,「電影對於觀眾有極大的吸引力,因為它再現出來對某種真實的印象(impression
of reality),而這種真實印象則是由作夢的情境強化;電影創造真實感,但這種真實感卻是一種整體效果,它創造觀眾,卻不受真實的完全制約」(林彥甫,1996:19)。
此一說法,與將電影視為一個「文本」(text),並將其置入特定歷史中加以理解的研究取向有密切關係。所謂的「文本」,是指任何寫下來的、視覺上的、或語言上作為「溝通」的媒介物,包含了書本、報紙、或雜誌上的文章、廣告、演說、官方文件、電影或錄影帶、音樂中的歌詞、照片、布料或藝術品等等(Neuman,2002:501) 。文本作為一種「社會實物」,透過文化生產的方式呈現在世人面前,發生社會效應,當然,自有它的理論基礎。換句話說,任何實物都一定是文化的產物,都是在一定情境之下某些人對一定事物的看法的體現(陳向明,2000:257)。
將此一說法用於看待恐怖電影,就會有不同的解讀視野;通常被視為是消費產物、超現實表演的恐怖電影似乎與我們無關,只可能發生在觀影經驗之中一筆代過。但是Wells(2003:7)曾經指出:
恐怖片的歷史,在本質上就是二十世紀的焦慮史。童話、民間傳奇和哥德派浪漫故事強調舊世界的憂慮,現代恐怖片卻勾勒出新世界的恐懼,並以工業、技術和經濟決定論的基本理論,來描繪新世界的特徵。因此,恐怖片比其他任何電影類型更質疑改革的深層效果,也更能夠回應社會、科學和哲學思想新近形成的重要論述。
恐怖片利用了當代對於「恐怖」、「恐懼」的認知效果來顯示戲劇張力,反之,它也是一部紀錄人類社會心象的歷史。而這裡有必要細緻區分「恐怖」與「恐懼」的概念,以理解它們的不同作用與效果。「恐懼」在心理學上是一種個體因受到足以產生驚嚇刺激而應對出來的生物行為,透過它,個體得以產生「防衛機轉」,如身體受到傷害會做出反射性的防衛動作一般,對於個體而言它有解釋環境、保護自我的效果。但是,在恐怖片的營造裡,它就不只是單純的刺激反應而已。這裡並非說,由觀看恐怖片所產生的恐懼反應不是生物性的,而是指,「恐懼」透過特定歷史文化的條件而轉換成一種社會認知系統,在這樣的體系中,重點不是「恐懼」本身的「刺激─反應」過程,而在於恐懼所承載的文化意義。
著名的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家與流行文化觀察家茱蒂斯•哈柏斯坦(Judith Halberstam)就說:「恐怖是一個體系(就像心理學)而不是一個特殊的個體,恐怖的惡是如出一轍而且難咎其責的」(Halberstam,1999:1)。而喬埃斯(James Joyce)就認為「恐怖」的定義是:
當某項嚴重且持續的苦難盤據了人們的思維,並使其對於引發苦難的理由牢記在心,這種感受就稱為恐怖(Wells,2003:2)。
於是,我們可以把「恐怖」視為是一種長期造成人心苦難的集體癥候,而「恐懼」則是對於它的反應。因此,恐怖片所企圖營造的,便是一種使人產生「恐懼」而不失娛樂化的文化體系,它使得「恐怖」可能不斷地被延續,「恐懼」只是它得以作用的媒介而已。恐怖片利用了如此的敘事手法,把我們日常生活中不時遭遇的危難、無法以科學解釋的經驗(如東西不見了又出來)加以擴張,也象徵著人類在超出理性範圍之外可能轉向超自然力量解釋的觀念,是一直存在於人類社會裡面的。電影理論家羅賓•伍德曾說(焦雄屏,1994:195):
恐怖片真正的主題是掙扎、了解我們文明所壓抑或壓制的事物。這些被壓抑、壓制的事物,如同我們的惡夢般,以戲劇化的姿態,重新被視為令人恐怖及害怕的對象,所謂「快樂的結局」,即是恢復壓抑狀況的典型。
也就是說,恐怖片透過對文明限制的顛覆與破壞,來達成人類潛意識當中對理性之外的迫切反動,促成一股批判性的視野,進而邁向社會實踐的可能。另一個英國電影理論家Andrew Tudor就曾經對於恐怖電影當中的主要敘事方式做了一種表述(Tudor,1989:83):
表一、恐怖電影敘事的基本對照
|
已知的 |
未知的 |
|
生命 |
死亡 |
|
每日的現世生活 |
超自然 |
|
正常身體 |
異常身體 |
|
人類規範(地球) |
變異的、不同於人類規範的(太空) |
|
有意識的自我 |
無意識的自我 |
|
常規性慾 |
異常性慾 |
|
社會秩序 |
社會失序 |
|
神智健全 |
瘋癲的 |
|
健康 |
疾病 |
|
文化 (優良的) |
自然 (劣質的) |
(本研究翻譯自Tudor原著「Table 5.1 Basic opposition
in horror-movie narratives」)
由上表可以得知,恐怖電影的敘事基礎是源自於二元對立,恐怖片推陳出新的展演,象徵著人類行至高度現代化的社會之中,仍然對未知的事物或他者感到恐懼,甚至將之具體化以便「設法解決」(如鬼物),並將這樣的心理、社會需求投射在日常生活儀式(如牽亡魂、祭祖)、言說(鬼故事)、人際互動(扮鬼臉)等面向當中以取得抒解(或理解),在恐怖片的敘事結構當中,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見這些需求的再現與實踐,也就因為如此,恐怖片不單只是過度的消費產品,更是進行社會觀察的施力點。而且在恐怖電影具有比其他類型電影更「超現實」的表演方式,它所帶動的符號意義更能把上述「電影創造真實」的宣稱加以對照,看看電影如何把人類無以言說的恐懼以符號創建出來、進而取代「恐懼的本源」,是恐怖電影做為社會實踐的重要因素。
第二節 布希亞「擬像」理論與恐怖電影的對應關係
後現代美學最典型的表現,不是諷刺性的模仿,而是擬仿(pastiche),一種空洞而中立的模擬,沒有原創與神秘性,可以說是朝向「文本互涉」與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說的「任意生吞所有古老風格」的方向邁進(Stam,2002:408)。李黛顰(2004)就曾經指出後現代主義的具有「多重不確定性(indeterminancies)解構
、普遍內存性(immanences)──人運用自己創造的象徵記號建構其宇宙,虛構與紀實的混合」的特質,在「普遍內存性」的面向上,則特別符合布希亞的宣稱。
後現代主義去除原點(original)、注重符號運動的模式,一般被視為是摒棄馬克思(Karl Marx)以生產關係作為社會形構的論點,而將「符號」的象徵性力量做為交換客體的社會特徵。而法國社會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就是後現代主義 中的主要大家(雖然他自己不願以社會學家自稱),他對於電視、廣告等媒體的社會作用,有獨到的「擬像」分析論點,也使得後現代的虛無美學理論化,甚至被引用到電影研究的領域上。Stam(2002:
408)就曾寫道:「後現代主義,像是一種論述的框架,藉著強調風格化的轉向,形成各種形式的電影,而豐富了電影理論與分析。」
對於布希亞而言,新時代的特點就是仿真,也就是經由仿真的過程,原先以物質生產做為社會動力,現在已經被符號的生產與擴散所取代,他並在1983年提出了「擬像」變化的四階段,符號便藉由這些過程無限度的擬仿,生產出無數個「擬像」(Stam,2002: 410):
第一階段:符號反應出基本真實
第二階段:符號掩飾或扭曲事實
第三階段:符號使得真實缺席
第四階段:符號只是擬像,也就是一種純粹的模擬,與真實沒有任何指涉。
而到底什麼是「擬像」?簡單的說,就是一種「沒有原本的副本」(a copy without
original)( E.C.Cuff等,2003:382),它不依靠著複製真實來確證自己而獨立存在,甚至成為真實的一部份。明報(2003)曾經對於布希亞的「擬像」有以下的註解:
但隨著資訊社會、高科技和大眾傳播的升級,消費由手段變成目的、影像符碼以幾何級數自我繁衍,其結果不是傳遞信息而是意義被否定掉,個體被浸染於同一化的集體中,真實與非真實之別徹底瓦解。所以,他有一名句為「影像的惡魔」 (the evil demon of images),他稱之為「不道德」(immoral),不道德的因由是,影像不是以意義來迷惑眾生,相反卻以一種無可抵抗的傳染病方式倍增,成為意義和「再現」的消失場所。
也就是說,在擬像的世界裡,「再現」本身也可能是虛無的、不牽涉任何本體真實,因為擬像使得真實缺席並進而取代了真實,這是後現代社會中一個很大的轉折,由於大眾傳媒的介入,使得螢幕上的影像才具有符號意義,成為唯一的真實所在,以布希亞的話來說,就是「符號作為真實與超真實」(signs as reality and hyperreality) ( E.C.Cuff等,2003:382)。而布希亞也把「擬像」的四個演變階段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加以檢視(謝鴻均,2001):
一、文藝復興以前,社會的階層體制是真實的反應,符號乃被限制和固定在社會的階層、責任和義務上,在這裡,流行系統並不存在,社會的變動與符號的使用錯誤(高於或低於一個人的地位)皆會受到懲罰。
二、文藝復興(十五、六世紀)到工業革命(十八世紀末期)之間,中產階級的秩序使社會相對地起了變動,流行誕生了,符號的競爭繼承了法定的社會秩序。符號被解放了,它不再指稱著義務,而是指稱著被生產出來的所指(向社會地位、財富、威勢這些意義)。大部分的階級都進入了這一套符號交換。但其偽裝是可查明的,因此這個時期的擬像是「偽飾」或「曲解的真實」。
三、工業時期(十九世紀)因工廠的大規模生產符號,符號成為重複的、系統的、操作的,並且使得所有的個體變成同一個樣子。符號所指稱的是不實在的,而人們為了要累積符號,所需要的即是金錢,而非社會權力。這時真實變得不再重要,擬像在此掩飾著不存在的真實。
四、布希亞說,二十世紀是擬像的世紀。在科學與資訊技術的大規模進步下,數位化、遺傳學和模控學(cybernetics)乃是擬像發揮作用的關鍵點。
在布希亞將擬像出現的脈絡加以切割的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對馬克思唯物論的棄絕,雖然他把電子媒體視做一種在消費社會當中使大眾去除人性的觀點,仍然有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異化勞動的譴責的影子(儘管他自己仍然宣稱要摒除馬克思不合時宜的理論架構)。布希亞在他自己的著作《波灣戰爭不曾發生[1]》裡,就引用擬像的概念把波斯灣戰爭形容是一次「非戰之戰」(non-guerre),來彰顯他對於電子戰爭的批判,也就是一次擬像的追逐戰爭(Baudrillard, 2003: 29-30):
我們已經不再處於從虛擬過渡到真實的邏輯裡,而是處於一種藉著虛擬嚇阻真實的超真實邏輯裡。………為了逃避真實性的劇變,我們選擇虛擬性的逃亡(逃亡於虛擬之中),其中,電視便是那萬能的虛擬之鏡。
他主要是在批判戰爭已經走向「在家收視」的消費產品,而不是在「實質」上像發動戰爭者所宣稱的任何豐功偉業。在這本《波灣戰爭不曾發生》以及《擬仿物與擬像》當中,他把電子媒體的後現代特性描繪的淋漓盡致,也可由其中找到布希亞對於「擬像」觀點的立論基礎,並加以移植到電影研究的領域。事實上,布希亞本身也是個電影迷,他第一部看的紀錄片《休士頓,德州─大南方》(1956)就是由恆軒巴赫(Francois Reichenbach)所執導的戰爭片,在片中,為求逼真不惜中斷真實軍隊的支援向菲律賓借調直昇機,片中或真或假的戰爭符號也開啟了布希亞真實「內爆」(implosion)的概念(Horrocks,1998:128-129)。在《擬仿物與擬像》一書中他進一步談到電影「從奇幻到神話,從寫實到超度現實」的特性(Baudrillard, 1998:
99),以他的分析而言,電影本身已不是歷史的敘事體,「歷史的危難被巨大的中性化所驅趕」,成了「我們失落的指涉物」(Baudrillard, 1998: 93),當歷史於電影中退卻或者電影本身不再宣揚歷史,也意味著「神話」的切入,也就是擬仿歷史的誕生。他更進一步指出(Baudrillard,
1998: 100-101):
電影剽竊自身,再翻拍自身,重演它的經典之作,重塑它的原初神話,以更完美的身段再造默片。所有一切似乎都合乎邏輯─電影被自身之為一個遺失的客體所蠱惑,正如同我們被真實之於一個遺失的指涉物所迷眩。在以前,電影與想像性─這裡所指的是創新性、神話性、非現實性,包括它自身技術所能達到的幻異屬性─的關聯,是活潑、辯證性,完滿且戲劇性的關係。而在現今,電影與真實性的關聯,卻是某種倒逆的、否定性的狀態。……就在電影性或者電視性的超度現實感,電影試圖要抹銷自身。
在此時刻,電影已經不再是反應現世的絕對表述。一篇網路專文也談到,「彩色電影作為最典型的後現代文化形態凸顯了後現代的平面模式和生命本能,也就是性與暴力(麥香紅茶,2004)」,而再拉到恐怖電影的討論上,剛好「性」與「暴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於是就產生了一種意義新解:恐怖電影將世俗的存在物虛構化,透過敘事把性與暴力轉化成稍縱即逝的光點剪影,棄絕了兩者本身的社會意義,而將其變成虛構體系的一環,賦予了它們除罪化的符號光環。在布希亞的擬像釋意裡,指稱的便是這種「意義內爆」的現象,而有趣的是,恐怖電影正是解釋他的理論的絕佳示範,因為在本身虛構性就很強的恐怖電影中,「意義」人為化的想像模式不在話下,到了後現代的時代裡,意義除了是流動的之外,更是沒有任何本體的,恐怖片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符號,要的是創造足以產生恐懼的意義以及面對恐懼的新態度,甚至這個意義在之前的文化體系中從來沒有出現過。從《鬼打鬼》利用茅山術對付殭屍,到《雙瞳》片中由梁家輝飾演的黃水土透過道教圖的拼湊循線找到被害者,被視為是理性科學的西方式演繹,可以看到由「專家」到「自己」與鬼物抗衡的軌跡,虛擬的電影符號讓我們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對抗(或掌握、理解未知、對抗鬼物,看似理性的背後,也載負著意義被重新建構的現象,因為我們永遠無法得知當鬼物侵襲我們時的反應採取,以及鬼物是否可透過理性模式加以消解的「真相」。
在這個層次上,恐怖電影曝露出「虛構與紀實的混合」的特性,而電影發展成大眾消費文化的一環,也是使這種價值觀大量流通的因素。符號流通代表著權力某種程度的瓦解,電影同時具備了符號價值以及大眾文化的一角,透過電影,或許它除了「再現」的功能外,更是創造符號、價值的源頭,身為觀眾所看到的,可能不只是現世社會的表徵,還是新的未來世界與「虛構的真實」。
第三節 港台恐怖片的演進脈絡
一、香港篇
一般而言,早期美國恐怖片的發展深受德國表現主義的影響(聞天祥,2000:75),並且從1920年代和之後的好萊塢模式的電影敘事來看,它對於世界電影來說是過份玩票卻又具主宰性的執牛角地位(Kleinhans,2001:25)。好萊塢身為全球電影重鎮,典型標誌的美國電影大片正以經濟協約的方式進入輸入國(尤其是東亞、東南亞,其中包括中國、台灣、泰國、印尼、菲律賓等「電影邊陲國家」),安裝視頻軟體的聯網電腦更是可以即時從網上下載最新的好萊塢影片,跨國集團在獲取鉅額經濟利益的同時,實際是傳輸著以名牌為主導的西方消費價值觀念,透過以片段閃現的MTV,迅速剪接的廣告衍生出迷幻與瞬間呈現的現代生活碎片,好萊塢英雄形象的塑造正有力的爭奪著對大眾意識的主導權(李曉明,2003)。而如果我們像多數人所說的那樣,認為美國的麥當勞文化(消費文化)是實際上的文化霸權,那麼這個問題實際上就轉換成了文化現代性的擴張問題(陶東風,1999)。
以恐怖片的類型為例,把時空拉到1930年代來看(當時正是好萊塢崛起的十年間),從中國第一位恐怖大師馬徐維邦起,不難發現在他的《夜半歌聲》(1937)到《瓊樓恨》(1949)有承襲美國恐怖電影的風格,但是卻也加入了大量中國倫常以宣稱華人世界的鬼神觀(聞天祥,2000:75)。華語世界的恐怖電影就在這樣一種與西方論述相互依存的模式底下發展出自己的表演風格,以香港為首的創作圈更奠定了特殊的「功夫片」類型,1970年代李小龍的電影系列更將「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的豪語發揚至西方,直到今日,功夫片的類型仍是香港、中國演員進軍好萊塢的利器,同樣的,它也是在1980年代中期促成《鬼打鬼》、《暫時停止呼吸》系列等「鬼片」以不同於西方表演模式來推廣華語恐怖電影的基礎。所以談到港台恐怖片的發展,不能不從功夫片的影響說起(台灣又有不同的發展模式,將分開討論)。
在第一章談到港台恐怖片的歷史背景時已經指出,在1980年搭功夫武打片便車而大行其道的《鬼打鬼》,是為恐怖神鬼片融合武打元素加以展現的濫觴,爾後在1985年《暫時停止呼吸》系列更是華語恐怖片當中一個經典的類型模式。
《暫時停止呼吸》系列塑造了如林正英等於茅山道長的個人表演定位,也使得遇到殭屍要摒住呼吸、於其額頭上貼符咒、桃木劍趨鬼的類型模式加以發揚光大,相較於此時期延燒整個好萊塢1980到1990年代的《十三號星期五》系列來說,類型化的程度並不遜色,甚至此一類型的電影被通稱為「靈幻電影」,可以想見當時的殭屍片盛況。陳明輝(2003)曾經把殭屍片做了如下敘述:
“殭屍片”其實是“鬼片”的一種。香港電影裡的所謂“殭屍”,現在比較流行的說法是源於過去湘西民間的“趕屍”風俗。相傳湘西沅江上游一帶,漢人客死異鄉後,按照習俗其屍體必须運回家鄉埋葬。但在崎嶇山路上借助車馬等運輸工具運屍耗資巨大,於是就有所謂的“法師”創造了“趕屍”這一行業。法師在前面帶路,屍體額上貼着黄纸符,一跳一跳地跟着。有人揭 穿所謂“法術”只是障眼法,真相是由兩個人輪流背屍體,由於專挑夜晚上路,别人遠看就像是屍體自己在行走。香港電影人以這些民間傳說為藍本,再结合明清小說裡有關鬼怪、屍變等光怪陸離的記載,創作出一系列殭屍電影。片裡的正派角色大多是以“墨線、糯米、黄纸符、桃木劍”為法寶的“茅山道士”,至於反派,在香港這麼一個東西方文化交匯地,殭屍電影也受到西方吸血鬼文化的影響,許多電影裡的中國殭屍雖然穿着清朝服装,但同樣尖牙利爪、喜吸人血和懼怕陽光。
由上述可知,這種類型電影反應出華語世界在看待鬼物的時候有別於好萊塢的觀點,卻又借鏡於好萊塢。可是因為之後繼起了一陣跟拍風潮,使得殭屍片失去新意,在1991年的《一眉道人》之後,殭屍片算是風潮已盡,主演道長的演員林正英在1997年辭世後,就一直後繼無人,沒有人再擔起飾演「道長」的經典角色責任。
但有趣的是,在1987年,當殭屍片開始走紅之際,由徐克取材自李翰祥於1960拍攝的《倩女幽魂》,亦承襲了80年代集恐怖、武打和逗笑於一身的混合類型鬼怪片之精神,徐克加入了愛情的元素來側寫人與鬼界的相同之處,並將敘事模式本地化與通俗化,並引進新科技讓電影視覺效果朝向國際化,使新版的《倩女幽魂》開始在國際展露頭角(
可是必須注意的是,90年代以後的香港恐怖片類型有了雙線操作的趨勢,一是上述所說的延續「暫時停止呼吸」、「倩女幽魂」等片的黑色幽默鬼片,另一軸線卻是殘酷的「社會寫實片」。
先來談談前者。在第一章背景簡述時已經提到,《陰陽路》系列是開創90年代恐怖喜鬧片的始祖。此一系列從1997年開拍了近二十集,每集都將生活中流傳的鬼故事、宗教儀式、傳說、惡作劇做為敘事主題,並將現代人可能遭遇的生活壓力與鬼神之說加以聯結,使整個《陰陽路》系列像是一本現代版的聊齋誌異,雖然它也充滿著香港電影為追隨資本主義、急欲開創商機而浮濫開拍的批評,以及對系列式電影信心的遞減效應,但仍然不失為是一套系統化的鬼神表述,也是一部值得分析的文化產物。伊素(1999)曾經對於《陰陽路五之一見發財》做了以下評論:
邱禮濤(導演)愈拍愈得心應手,而且把各樣的情懷利用鬼片類型大抒特抒,片中的鬼已經是各樣人類情誼的象徵,這趟一見發財大幅增加的警世意味,同時間把各種六十年代的粵語片符號引入,重提賭仔誤己誤人的憾事,藉六十年代手停口停的寶貴經驗,暗喻投機的機會主義者的危險,放棄賭仔性格而重投腳踏實地的做人處世原則,實 是香港現況的最大感觸。
我們不妨將《陰陽路》的現代傳奇視為是一種「都市神話」的表徵。根據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對於「神話」的結構研究來看,神話有其真實的深度意涵,不能用表面的內容以簡述之,他認為即使是身處現代文明的我們,行事基礎仍舊有可能與神話時代的邏輯有相仿之處,而且,這些原因卻不一定可以用社會化的專業字眼得到合理的解釋(E.C.Cuff等,2003:259-260)。一個文化或是一群文化所特別中意的神話、信仰與實踐都會進入這些文化的敘事當中,爾後再加以深入、強化、批判或覆述再製;透過敘事的主題或形式風格的轉變,我們或許可以了解某個時期的社會變遷(Turner,1997:102)。《陰陽路》系列正是利用了此種特質,將神話或鬼故事當中的二元對立因子強化,營造出「現代理性 / 遠古未知」、「生 / 死」」、「鬼 / 人」等敘事結構,正是透視了傳統鬼神觀仍然支配著物質生活,並藉著恐怖事件來指涉人類互動的象徵性殺戮與隔閡。「鬼神」本身是否「真實」存在則一直不是神話所要記載的正史,透過儀式性的互動過程,才是鬼神的言說形象得以複製、流傳的動線。
而在同時崛起的「社會寫實片」,反而使香港「恐怖片」的定義不再侷限在超自然的鬼物,而是「真實」的犯罪事件──這個主題其實早在好萊塢恐怖片中發酵過。
在1960年代以後,好萊塢恐怖片出現最大的恐懼,就是對「他人」的恐懼 (Well,2004:22),1974年好萊塢就以實事改編成了《德州電鋸殺人狂》(Texas Chainsaw Massacre),是為殺人狂電影的濫觴(艾爾,2002:33)。從此,「殺人狂」所造成的電影元素便不斷重製於銀幕上,而造型也越來越經典(如《十三號星期五》系列中殺人魔傑森的曲棍球面具)。儘管在Crane(1994:2)的觀察中,恐怖片已由早期著重血腥轉向心理驚悚,避免不必要的流血(avoiding
unnecessary bloodshed),但是當1979年《德州電鋸殺人狂》把骨頭與肉塊塑造成超現實生活空間的屠宰場調度,顯示出它對身體以及人性以身體作為實體憑證的蔑視之際(wells,2003:143),在好萊塢的恐怖類型電影中仍以摧殘身體為恐懼來源,Crane所觀察的演變則是接近90年代之後的事。順到一提的是,約在1974-1975年間,砍殺式的電影(slasher
films)在好萊塢影壇中發酵,如上述所說的《德州電鋸殺人狂》、《月光光心慌慌》(Halloween)、《十三號星期五》、《半夜鬼上床》等片都是經典例子,可是這些「B級恐怖片」都是小預算製作,到了90年代,才忽然變成美國電影的主流,它們所分享的價值觀,就是對女性身體的摧殘,以及男性生吞活剝(devoured)她們的表現(Edmundson,1997:3)。這些哥德式[2]的恐怖(Gothic horror)成為美國恐怖片的敘事重點,Edmundson(1997:5)更進一步指出,恐懼成為世紀末人們普遍的娛樂形式,在新聞、每天的報紙、電視脫口秀裡面,甚至是一種治療我們的方式。這些現象恰好與布希亞對於媒體分析的論點不謀而合,「恐懼」最重要的不是原先所指(signifier)的意義,在布希亞後現代的觀點裡,意義是內爆的(imploded),「恐懼」在後現代社會的符號象徵已經不是單純指涉生理性的刺激反應,而形成多元性、無涉真實的符號語言以供消費。這些脈絡也同樣出現在港台恐怖片的演變裡,在港片中,約在90年代的「社會寫實片」也探討了「身體摧殘」的主題,對於女體的剝削形成男性快感的來源,這類恐怖片除了單純的恐懼傳遞效果以外,也類似Edmundson所說的「準性慾」(quasi-sexual)電影。
在1993 年上映的《人肉叉燒包》有著契合於西方強調摧殘身體以達恐怖效果的敘事結構。這部改編自1986年澳門所發生的真實殺人慘案的電影,雖然被大多數的討論歸類為「三級片」,不過劇情中強調肢解以及對身體無限度壓迫的形式(如強暴女性受害者並予以殘殺),後來被許多跟風之作所模仿(如《人肉叉燒包2天誅地滅》、《人肉玩具》等等),使得香港早期以黑色幽默做為「鬼片」或「恐怖片」的敘事手法遭遇改造,亦使得由「真實事件」改編的故事比起遠古傳說更能貼切人心,讓人產生恐懼感,而不論所謂的「真實事件」是否如實存在。《人肉叉燒包》的出現讓香港「鬼片」與「恐怖片」的類型分類更加難分難捨,它所令人畏懼的不是鬼物,而是自己隨時可能變成受害者的真實臨場感。所以嚴格上來說,香港恐怖電影的發展不能棄卻此一類型電影的討論,在西方,同樣殺人類型的電影,早已納入在恐怖片的範疇裡廣泛辯論,而不論施暴者是否為超自然的鬼物。《沉默的羔羊》導演強納生•德米(Jonathan Demme)就曾針對西方自1960以後的恐怖片元素這麼說過(Wells,2004:22):
此時(指1960年代後),唯一能夠徹底且毫不費力地代來真正恐怖的,就是連環殺手(serial
killer)。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任何人都可能因符合某個連環殺手所尋找的作案對象而淪為受害者。
當「受害者」這個名詞大量出現在因犯罪事件而產生傷亡的媒體報導時,人們的恐懼感將比遇到鬼物來得更真實。這裡所說的,也就是電影再現了社會真實所造成的效應。提到另外一個例子,在
二、台灣篇
說到台灣「恐怖電影」,或許是一項無法成立的討論。台灣身為華語圈的一份子,但是其電影工業幾乎是消聲匿跡的,早年靠《好小子》(1986)、《報告班長》(1987)系列開創國內電影市場的榮景早已不再,何況是討論「恐怖片」這個類型的電影。所以在探討台灣鬼片之前,必須先對台灣特殊的電影工業環境以及政治背景作一番整理,雖然本研究並不把重點置放在文本製產的面向上。
在1974年,姚鳳磐在台倡「鬼」片,計有《秋燈夜雨》、《秋夜孤魂》、《寒夜青燈》、《鬼琵琶》發片,極盡聳動之能事。內容不外乎包括冤魂索命、情慾糾葛、貪財懲戒、披頭散髮青面獠牙的鬼魂,或增加音量嚇人,算是台灣鬼片最早的濫觴(光影紀事,2004)。嚴格說起來,台灣並沒有明確的「恐怖片」類型,許多敘事模式其實與港片早期以武打、黑色幽默來拍攝恐怖片的軸線大同小異,但自從1989年解除外片進口的機制之後,台灣本土電影逐步失守[3],進而變成好萊塢片商的大本營之一;歷經了好萊塢全球行銷、西方影片本身具吸引力以及國內投資商撤資的多重打擊之下,台灣本土電影市場已經沒有常態的立足之地,「電影」本身成為台灣文化缺席的一部份。
在這樣體質奇差的環境裡,要討論台灣「恐怖類型」的電影似乎不若香港清晰,所以在針對類型討論之前,必須先知道台灣電影所遭遇的結構性問題。台灣電影成為電影發行商唯恐避之不及的票房毒藥,肇始於80年代末期開始,台灣電影製片事業急速萎縮之後,台灣電影製片的投資早已將資金轉到香港或中國大陸等影片的攝製上(劉現成,2001:188)。這個情況到了現在只有變本加厲而不見好轉,加上好萊塢全球化的電影行銷、香港電影工業逐漸被好萊塢收編的事實,台灣電影幾乎已經沒有生存空間,在華語圈的電影創作工業台灣是孤獨而備受冷落的,只靠一些國片輔導金來拍片。
90年代後期,台灣本地投資者視華人地區自製的影片猶如洪水猛獸之餘,台灣每年僅有十餘部左右的影片產量,幾乎全得靠政府輔導金才得以籌拍;台灣的製片公司都將以爭取電影輔導金為年度重要業務,長久下來市場機制盡失,如果可以進入影展市場,不論是參賽或參展,皆屬萬幸,否則連本土上映的機會都沒有,更別談走出台灣以外的電影市場(劉現成,2001:189-190)。
事實上,華語片市場的沒落不只是台灣電影的專利(聞天祥,1999 :100)。香港片繼周星馳創造出「無厘頭」的搞笑片風潮[4]之後,也曾經走入低潮,至少在台灣市場不再有吸引力。可是其擅長的動作片卻是華語區域內的翹楚,甚至被好萊塢電影公司網羅,證明在全球影業中,武打動作影視節目是華人社會中所獨有,這種影視節目類型創造出香港在武打動作片上特有的人才與專業知識,使得香港電影仍具有競爭優勢(鄭呈皇,2000:181)。
但台灣電影就沒有這麼幸運。早期在70年代,電影是被左翼知識份子所鄙薄的大眾文化之一。對於當時的左翼知識份子而言,國民黨在二次戰前即整編了電影,制訂電影檢查法、設置檢查機構、發展出一套消滅左翼電影的措施,以及國民黨政權敗退來台之後攝製政策性電影,政權穩定時放任了娛樂性電影的生產(郭紀舟,1999 :182),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電影被視為是一種靡靡之音,以致於當時傾向社會主義、宣稱反資本主義的左翼知識份子發起「拒看國片」的運動。可是也有人為這種極端輕視大眾文化,過於用政治的眼睛看待文化結構,而可能喪失對其批判力與滲透力的傾向感到疑慮。當時重要的左翼刊物《夏潮》[5]曾經有署名為「傅心名」的人士寫了一篇〈從「拒看國片」談電影與知識份子〉的文章,提出下列不同看法(郭紀舟,1999
:183):
知識份子應以「關心」或「介入」的方式參與電影文化……到有一天,許多富有改革意識的知識份子再來指責電影界固有的意識形態,再來抱怨國內的環境,以及廣大的群眾心理形態,再不是事倍功半就是太遲了。
很不幸的是,70年代的箴言竟然成真,雖然因素不再是知識份子為政治立場來抵制國片,但台灣電影目前所遭遇的結構性困境更是雪上加霜。台灣歷經了電影污名化的政治時期,一直到80年代末期移資大陸或香港的政策性衝擊,可以說是內憂外患,也使得國片繼朱延平軍教片、郝邵文的兒童武打笑鬧片之後,幾乎是不見天日,只能在小型獨立戲院、或靠小型影展聯映。
大致談完台灣整體的電影工業之後,再來試論「恐怖片」在台灣的發展。在1980年代時期,台灣國片靠著《桃太郎》、《新十二生肖》等神怪片勉強與「恐怖片」沾上邊,但相較於香港《暫時停止呼吸》系列,這些台灣「恐怖片」更具有民間傳說的特質,甚至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童話或神話故事,所以沒有觀影經驗斷裂的阻隔。爾後歷經國片電影市場幾乎消失的年代,「恐怖片」的台灣版更是少之又少。有趣的是,「恐怖片」以「靈異節目」的變體模式悄悄進入一般家庭收視習慣裡。根據電研會的報告指出,台視的綜藝節目「玫瑰之夜」於
可是,畢竟電視與電影是不同的機制,雖然靈異節目的出現填補了「恐怖片」、「鬼片」在台灣電影界的空席,但仍然不能將其視為是一種台灣影業的環節,因為它們對實質的電影工業沒有經濟助益。台灣電影對於「恐怖片」類型的蓬勃現象,大概到1999年才真正在台灣發酵(聞天祥,2000:76)。但可惜的是,恐怖片類型的開拍一直沒在台灣形成風潮,許多層面是來自於大環境與資金的限制,加上出國參賽(展)的「藝術片」類型比較容易獲得政府輔導金資源的前提,「恐怖片」這種「次級類型」電影還是沒在台灣本土電影圈持續發展。由王小棣於1998導演的動畫片《魔法阿媽》,講述一個具有通靈能力、能看到鬼的老婦人與其孫子交織出的遇鬼經歷,是本土少見以動畫方式來陳述傳統華人鬼神觀的影片。但金馬獎評審卻嫌它「迷信」(聞天祥,2000:76),反應出台灣電影界的生態,是基於一種「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的考量,而不是藝術與現實的互動關係。爾後,1999年唯一一部與「鬼」扯上關係的本土影片,是由吳宗憲導演的《校園有鬼之神探二又二分之一》,但與其說它恐怖,不如說是一部笑鬧綜藝片,也幾乎沒有觀眾將之納入「恐怖片類型」來加以看待(聞天祥,2000:76)。
到了2002年,由陳國富監製、執導的《雙瞳》算是台灣恐怖片的里程碑之作。長年以來,台灣的電影工業一直以製作小眾、受影癡及影評人讚賞的藝術電影聞名世界,《雙瞳》企圖打破此項成規,要將台灣電影朝向新的敘事手法、新的電影境界邁進 (雙瞳電影宣傳網,2002)。陳國富原是《徵婚啟事》的導演,由文藝片到恐怖驚悚片的轉換跑道,使他對於自我電影定位、以及「恐怖驚悚片」在兩岸關係緊張之下的特定意義脈絡,有了國族主義式的解釋(雙瞳電影宣傳網,2002):
……像我這樣的人就是無法拍一部一般的驚悚片……這不是故意的,而是我身上背負的包袱。我生長在一個充滿文化認同焦慮的地方,我們和中國大陸的關係像是一顆不定時炸彈,時時刻刻威脅著我們。同時,1987年開始,我們解除了戒嚴令正式邁向民主,這些都是很大的改變,需要時間去調適的。
蘇照彬[7]和我在寫劇本時其實根本沒想到這些,我們只想拍一部娛樂片而已。但是現在我回過頭來想,這些焦慮其實一直長駐在我們的潛意識中。某種程度來說,一部好的驚悚片總是反映了我們內心最深的恐懼。
《雙瞳》在行銷手法與影片本身魅力的加持之下,創下了國片近年來少見的票房佳績,但其中結構面的因素,也多肇因於跨海合作的技術整合,與英語演員的優勢。然而《雙瞳》的成功模式卻沒有複製到台灣電影的持續發展,2003年由朱延平導演的本土電影《搞鬼》就沒有這麼幸運。《搞鬼》是運用了早年軍教片的背景,加上當兵所流傳的鬼故事等集體記憶來營造詭異氣氛的影片,也啟用了新生代演員(如張善為、安雅、郭定文等人),可是仍然沒有造成像《雙瞳》這般的熱潮。其實,《雙瞳》與《搞鬼》都是藉由民間流傳的鬼故事做為敘事主軸,並加以改編了許多早已被人遺忘或根本子虛烏有的恐怖元素,來重新喚醒或取代恐怖的符號(如午夜12點不要看馬桶中的水倒影、雙瞳者會招致不幸等等),但後者延續台灣觀眾熟悉已久的軍教片背景,喚不起觀眾的新鮮感,加上由本土「延平影業公司」出資、缺乏跨海資金技術合作、上映戲院有限等因素,導致這部純粹由台灣完成的鬼片沒能得以突破重圍。
台灣在華語電影圈中的角色並不是直接生產者,而是「原料供應商」。近年來由台灣出身、跨海至西方或香港地區的影星越來越多,如舒淇、劉若英、楊貴媚等影星,甚至連蕭亞軒亦到好萊塢試鏡、田麗也將進軍美國(林美璱,2004)。除了影視歌星的輸出成為台灣影業的契機以外,投資各國的影視事業,而取得台灣的發行權,提高資金運作之效率,加強以華語圈為主的電影工業,漸次找回流失的國片觀眾亦是台灣影視發展的一種途徑(鄭呈皇,2000:181)。「恐怖片」的類型電影可依循《雙瞳》的映演模式,加強跨海合作,擴大資金與技術、人才的聯結,並且立基在以華人精神為主的編劇手法之上,一樣可以發展出屬於華人世界特有的恐怖片,又不失借鏡於西方論述的可能。台灣另類的電影工業發展,也可能賦予國產電影更強烈的後現代體現。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恐怖片的定義
根據政大廣電系系主
(一)恐怖片內容包含令人感到驚嚇或害怕的因素。因為在內容上,製造危險、傷亡或破壞,如天災或血腥暴力;或是正常形體或容貌出現扭曲變形,如腐屍、狼人、異形或怪獸;除此之外,呈現他人受難或驚嚇的經驗,也在恐怖片的定義當中。
(二)除以上條件外,影片中所營造懸疑、詭異或緊張的氣氛更容易令人毛骨悚然。成功的恐怖片會透過情節安排、音效、運鏡、剪接、演員的表情、化妝及特效等方面去營造恐怖氣氛,本論文所研究的港台恐怖片多屬於此類。
第二節 研究對象
依照港台上映年代排列,唯系列式電影以第一集年代為主,順序排列。
表二、研究文本一覽表
|
編號 |
片名 |
年代 |
出品/發行 |
出產地 |
|
1. |
鬼打鬼 |
1980 |
嘉禾 |
香港 |
|
2. |
暫時停止呼吸 |
1985 |
嘉禾、寶禾 |
香港 |
|
3. |
暫時停止呼吸續集 |
1986 |
嘉禾、寶禾 |
香港 |
|
4. |
新暫時停止呼吸3 |
1992 |
嘉禾、寶禾 |
香港 |
|
5.. |
正宗鬼打鬼之靈幻天師 |
約1985年後 |
學者 |
香港 |
|
6.. |
胭脂扣 |
1988 |
寰亞 |
香港 |
|
7.. |
倩女幽魂 |
1987 |
寰亞 |
香港 |
|
8. |
倩女幽魂2人間道 |
1990 |
寰亞 |
香港 |
|
9. |
倩女幽魂3道道道 |
1991 |
寰亞 |
香港 |
|
10. |
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 |
1993 |
聯登 |
香港 |
|
11. |
人肉叉燒包2之天誅地滅 |
1998 |
國際電影 |
香港 |
|
12. |
怪談協會 |
1996 |
學者 |
香港 |
|
13. |
猛鬼卡拉ok |
1997 |
嘉禾 |
香港 |
|
14. |
屍氣逼人 |
1999 |
王晶創作 |
香港 |
|
15. |
山村老屍I |
1999 |
寰宇 |
香港 |
|
16. |
陰陽路之六兇周刊 |
1999 |
潤萬娛樂 |
香港 |
|
17. |
陰陽路之七撞到正 |
2000 |
寰宇 |
香港 |
|
18. |
鬼片王之兇榜 |
1999 |
專業電影 |
香港 |
|
19. |
人肉玩具 |
1999 |
國際電影 |
香港 |
|
20. |
炭燒兇咒 |
2000 |
嘉禾 |
香港 |
|
21. |
陰風耳 |
2000 |
新潮社 |
香港 |
|
22. |
每天嚇你八小時 |
2001 |
思維娛樂 |
香港 |
|
23. |
恐怖熱線之大頭怪嬰 |
2001 |
美亞 |
香港 |
|
24. |
七號差館 |
2001 |
東方 |
香港 |
|
25. |
幽靈人間 |
2001 |
寰亞 |
香港 |
|
26. |
幽靈人間2鬼味人間 |
2002 |
寰亞 |
香港 |
|
27. |
異度空間 |
2002 |
星皓 |
香港 |
|
28. |
雙瞳 |
2002 |
哥倫比亞 |
台灣 |
|
29. |
我左眼見到鬼 |
2002 |
一百年電影 |
香港 |
|
30. |
見鬼1 |
2002 |
星霖 |
香港 |
|
31. |
見鬼2 |
2004 |
Applause pictures And MediaCorp.Raintree pictures聯合出品 |
香港 |
|
32. |
三更 |
2003 |
GOLDEN SCENE |
香港 |
|
33. |
咒樂園 |
2003 |
製作基地 |
香港 |
|
34. |
搞鬼 |
2003 |
延平影業 |
台灣 |
|
35. |
救命 |
2004 |
星皓 |
香港 |
本研究收集以上樣本,分別基於下述理由:
(一)建立典範的影片類型,可供「鬼怪」形象的後現代轉折研究:如《鬼打鬼》(1)、《暫時停止呼吸》系列(2~5)、《胭脂扣》(6)、《倩女幽魂》系列(7~9)、《人肉叉燒包》系列(10~11)、《陰陽路之六兇周刊》(16)、《陰陽路之七撞到正》(17)
(二)系列式電影的跟風之作,用以參照當時所著重的表演論述模式:如《猛鬼卡拉ok》(13)、《山村老屍I》(15)、《鬼片王之兇榜》(18)、《人肉玩具》(19)、
(三)創造一時話題的強片,以分析與稍早鬼片元素的異同之處,以及抽離其中後現代文化的體現:《幽靈人間》系列(25~26)、《異度空間》(27)、《我左眼見到鬼》(29)、《見鬼》系列(30~31)、《三更》(32)、《咒樂園》(33)、《救命》(35)
(四)少數由台灣拍攝的鬼片: 《雙瞳》(28)、《搞鬼》(34)
(五)其他類,可由其中抽離出特定時期的「鬼物」後現代表現模式,用以補充文本分析的內涵: 《怪談協會》(12)、《屍氣逼人》(14)、《炭燒兇咒》(20)、《陰風耳》(21)、《每天嚇你八小時》(22)、《恐怖熱線之大頭怪嬰》(23)、《七號差館》(24)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採取「文本分析」法,針對以上35部自1980~2004港台恐怖片進行研究,且利用布希亞對於「擬像」的後現代分析觀點,抽離出港台恐怖電影在時空流變中,所呈現的虛實符號,來突顯華人鬼神觀的後現代轉折。
「文本分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長遠之前對於聖經的解釋,以及十九世紀的聖經「詮釋學」(hermeneutics)和文獻學(philology),與法國的「徹底閱讀」(close reading)、美國新批評派的「內在分析」(immanent analysis)(Stam,2002:254),但脫離不了的就是與「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有密切關係。結構主義者認為語言、事物及其所組成的意義之後,尚有「超越」的東西存在,但是文本從結構主義這裡得到養份之後,也獨立出自身的解釋力,由原先依循結構主義認為的「結構深層的同一性」,到後結構主義宣稱的「意義多元而無可參照」的脈絡,「文本」的詮釋面向也豐富了起來(夏春祥,1997:144)。既然如此,文本實物的分析就與語言分析有了區隔。語言主要依賴於「概念」的使用,但是文本實物更加依賴於「形象的召喚」以及物品本身的使用方式,語言分析約制於語言本身規則的運作,是一種以規則為基礎的認知方式,依賴的是人們對語言本身的「理性認知」;而文本實物分析依賴的則是一種「聯想模式」,其意義主要對應於人們日常生活的「實踐理性」(陳向明,2000:257)。也就是說,文本實物在分析的層次上,比語言更加不透明的把文化意義付諸行動(實踐),在此過程當中,人們將對文本的解讀方式變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而忘卻其中的實踐意義,文本分析所要揭示的,便是這種隱藏關係。
文本分析有「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兩條理路,前者著重在對於書面文句的再詮釋,後者則將「文本」置放在一個特定的社會脈絡之下去探討「文本與社會」的關係(夏春祥,1997:145-147),本文所進行的電影研究,便是採用後者。
文本分析作為文化研究的策略之一,其歷史可追溯至英國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CCCS)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首開其端的研究傳統(夏春祥,1997:146)。英國的文化研究關心於大眾文化或流行文化的部份,也就是上述所說「其意義主要對應於人們日常生活的『實踐理性』」,在實踐的過程當中,也正是與「文本」進行交互作用。因為,文化實踐是一種銘刻,如同拳擊手打鬥後所留下的身體印記,這就像Loic Wacquant所強調的;而任何文化也是現狀對於過去的再現,這些「再現形式」的演繹也是關聯到人類存在的現世行動之上(Wagner,2001:126)。
再者,文本分析的概念不只侷限在社會學、文學,對於傳播領域而言它也成為討論的主軸。重點在於,大眾傳播所進行的文化意義流動經常伴隨著社會實踐的意涵,所以可將傳媒視為是文化載體,那麼一來,傳播領域中的文本分析也具備了社會學的研究價值──如本文要進行的電影研究一般。黃靖惠(2003:81)指出以社會學角度去分析傳媒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共有四個面向:
(1)人文取向─以媒體文本為分析焦點,例如關切創作者的生活文化,但對於媒體訊息的效果則僅止於猜測。
(2)社會問題取向─把重點放在傳媒文本對閱聽者所產生的影響,尤關注媒體的長期效果。
(3)大眾傳播取向─同樣著重於傳媒文本對閱聽人的影響,但把焦點置放在特定媒體短期且立即的效果。
(4)產製文化取向─以媒體機構為分析單位,探討製產文本的機構組織文化或整體社會文化。
本論文所採取的策略,是將電影媒體視為一個「可供進行意義拆解與分析的文本」,將蘊含在電影再現中的文化觀點抽離出來,而非關注電影本身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因此屬於第一類「人文取向」的文本分析模式。
而上述已談到文本分析的歷史與其對社會互動的關係,將文本分析運用在社會研究的面向上,最重要的一點仍是透過文本進行對於社會的「詮釋」。而不管上述所說的「以社會學角度去分析傳媒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屬於哪一種取向,或是「人們如何在文本中呈現社會實踐」的議題,都在於強調文本分析是一種動態的詮釋過程,相較於針對訊息明顯內容加以量化、歸類、描述的「靜態式」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被視為彌補此法對於社會研究滲透力不足的選擇,Larsen就就曾在〈媒體戲劇內容的文本分析〉一文中,直接以文本分析來指稱質化的內容分析,且採用Kracauer的觀點,把文本視為一個整體並加以詮釋(游美惠,2000:17)。文本分析長期以來遭受「主觀寫作」的批評,許多慣常使用傳統研究方法(多是量化)的社會研究者認為,它是一種文學式的創作、評論,而不是科學的過程。但Fairclough也指出文本分析運用於社會研究上的四種確當理由(游美惠,2000:19),之所以提出這四項理由,並非強化文本分析的合法性、適用性,而是凸顯它在量化統計、質性訪談等研究方法之外對於社會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它所存在的研究基礎:
(1)理論上的理由:社會結構與社會行動是在研究社會時必要討論的重點,而文本提供了社會行動之擅場,社會學家在分析鉅觀結構時,也必須從文本獲得資料。
(2)方法論上的理由:文本分析能將研究的宣稱植根於文本的詳細特質裡。
(3)歷史的理由:文本的呈現方式可以視為社會變遷的指標,因為在不同歷史時空中會出現不同的文本。
(4)政治的理由:越來越多的文本(不只是媒體文本)有社會控制與支配運作其中,文本分析作為批判論述分析之一部份,有助於大家提升對語言的穿透批判力。
職此,文本分析提供研究者在觀察社會、與社會結構對話時的客觀基礎,絕非單一式、主觀式的寫作,本論文基於上述理由,採取「文本分析」針對35部1980-2004港台恐怖電影進行研究,企圖透過電影文本,挖掘20年間華人世界對於「鬼神」的文化觀點,呈現什麼樣的後現代態勢。
第四節 研究架構
主要的分析策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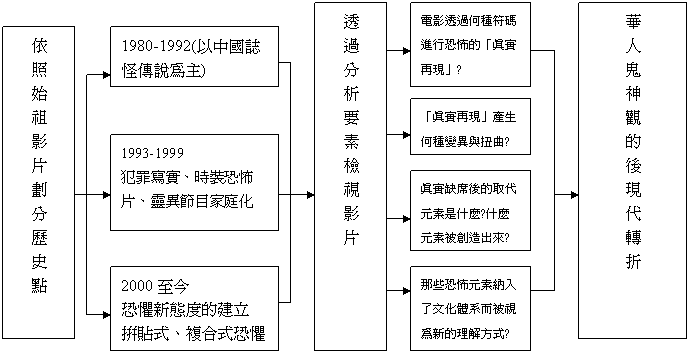
圖二、研究架構圖
第五節 研究限制
文化研究一直是一項龐大的交互辯證,沒有辦法加以窮盡。本論文針對香港與台灣的恐怖片加以研究,是基於兩地文化同質性的立場,但仍然有以下限制:
(一).「後現代」概念源自於西方,在移植到東方文本的討論上時,難免會招致理論適用性的質疑。而本論文所採取的後現代「擬像」觀點分析,是許多解釋華語電影的途徑之一,並且是立基在港台與西方社會都具有媒體消費與實踐的前提之上,唯有在相等或相似的社會力支持之下,才能進行理論分析。而電影作為世界最大娛樂消費體系之一的特質,已成為跨國的普遍記憶(經驗),本文基於以上原則,選擇電影做為華人後現代模式的再現擅場,並非指稱後現代觀點是華語恐怖片的唯一徵象。
(二)選取台灣影片過少:由於台灣電影圈情況特殊,幾乎沒有量產而穩定的恐怖片推出,所以本論文僅選取了近年來較熱門的《雙瞳》與《搞鬼》兩部片。台灣電影界雖然不景氣,仍不能抹煞台灣在華語電影裡的特殊貢獻,《雙瞳》便是跨海合作的成功例子,也帶有台灣身處在後現代境況中的分析價值,因此本論文仍把主題訂為「港台恐怖電影」研究,唯針對台灣地區的電影研究,仍有待日後的努力。
(三)當我們把恐怖片視為是一種可「再現」的文本,似乎就預示了文本與外在真實的指涉關係,但是這種關係的穩定度是可以質疑並解構的,「再現」並不是單純的鏡像,當電影成為一項人為的社會產物,它所呈現出的「再現」、所映照出的「真實」,就具有階段性並會流動,而本研究正是以這種基礎作為分析,並不企圖在「再現的本質」上做討論。
(四)本研究在分析層次上,將港台恐怖片的發展預設成線性歷史的狀態,並非堅守「目的論」的原則棄絕歷史本身的偶然性因素,本研究以為,電影做為文化生產的主體,與文化體系是相承而非主從關係,所謂的「線性歷史」是指時間的客觀性而言,而非忽略其間作用的文化、社會偶然性因素,本研究所揭示的向度僅是電影發展的眾多解釋之一,也是將電影視為能動主體的概念(文本的原初價值)因為,任何「目的論」的說法本身也是一種「目的論」,容易招致危險。
第六節 預期結果
透過反覆觀看文本,找尋出由承襲中國誌怪傳奇的敘事手法,到後現代擬像、拼貼式的恐怖片風格,藉由電影再現的前提整理出二十年間華人鬼神觀的後現代轉折,與其中文化遞嬗的面向。
初步參考書目
英文專書
Crane,
Edmundson, Mark (1997), “Nightmare
on Main Street-Angels, Sadomasochism, and the Culture of Gothic”,
Neale, Steve (2000), “Genre
and
Tudor, Andrew (1989),
“Monster and Mad Scientists-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Horror Movie”,
Wagner, Peter (2001), “A History
and Theo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中文專書
Baudrillard, Jean著,黃建宏譯(2003),《波灣戰爭不曾發生》,台北:麥田。
![]() ,洪凌譯 (1998),《擬仿物與擬像》,台北:時報。
,洪凌譯 (1998),《擬仿物與擬像》,台北:時報。
E.C.Cuff等著,林秀麗等譯(2003),《最新社會學理論的觀點》,台北:韋伯文化。
Featherston, Mike,劉精明譯(2000),《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南京:譯林出版社。
Horrocks, Chris著,王尚文譯(1998),《布希亞》,台北:立緒。
King, Geoff Z Tanya Krzwinska著,魏玓譯,《科幻電影奇航》,台北:書林。
Neuman,W.Lawrence著,王佳煌,潘中道譯(2002),《當代社會研究法》,台北: 學富。
Slater, Don著,林佑聖、葉欣怡譯(2003),《消費文化與現代性》,台北:弘智。
Stam, Robert著,陳儒修、郭幼龍譯(2002),《電影理論解讀》,台北:遠流。
Turner, Graeme著,林文淇譯(1997),《電影的社會實踐》,台北:遠流。
Wells, Paul著,彭小芬譯(2003),《戰慄恐怖片》,台北:書林。
艾爾(2002),《驚悚100》,台北:時報。
郭紀舟( 1999 ),《70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海峽學術。
陳向明(2000),《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陳儒修(2003),〈文化研究與電影研究〉,收錄在陳光興主編《文化研究在台灣》,台北:巨流。
焦雄屏(1994),《閱讀主流電影》,台北:遠流。
劉現成(2001),《華人傳媒產業分析》,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
中文期刊
Kleinhans, Chuck作,葉月瑜,劉慧嬋譯(2001),〈變成好萊塢?新紀元的香港電影〉,《電影欣賞》,19(1):23-28。
夏春祥(1997),〈文本分析與傳播研究〉,《新聞學研究》,54:141-166。
游美惠(2000),〈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在社會研究的運用〉,《調查研究》,8:5-42。
黃靖惠(2003),〈社會學對媒體閱讀人研究之啟示〉,《中華傳播學刊》,4:79-107。
聞天祥(2000),〈嚇不死你,就感動死你─淺談華語電影中的鬼〉,《聯合文學》,16(10):74-77。
![]() (1999),〈華語電影一九九八─蒙塵的一年(下)〉,《電影欣賞》,98:100-105。
(1999),〈華語電影一九九八─蒙塵的一年(下)〉,《電影欣賞》,98:100-105。
影響雜誌編輯部(1997),〈妖魅出櫃─你看見魔鬼的顏色嗎?東西方鬼片的主題視野〉,《影響雜誌》,87:16-28。
謝旭洲(1999),〈觀看恐怖片與觀眾的驚嚇反應研究:以日片《七夜怪談》為例〉,《民意研究季刊》,210:90-117。
羅燦瑛(1998),〈性暴力的文化再現:港台強暴電影的文本分析〉,《新聞學研究》, 57:159-190。
論文集
Parry,Amie著,涂懿美譯(1999),〈Judith Halberstam介紹詞〉,《第三屆性別政治超薄型國際學 術研討會「宛若TC」論文集暨大會手冊》,中央大學性 / 別研究室。
林彥甫(1996),《觀看恐怖電影的心理機制─以「認同」分析「半夜鬼上床」》,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佳玲(2000),《「香港 / 人」的顯影拼貼─析論「家」與「身分認同」的香港電影論述》,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呈皇(2000),《跨國傳播集團與台灣影視產業的競爭論述》,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網站資料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傳播中心(
光影紀事(1971-1980分年式歷史搜尋),《台灣電影筆記》,http://www4.cca.gov.tw/movie/history/taiwan.asp?sn=8(
伊素(1999/2/1 ),〈陰陽路五之一見發財評論〉,《香港電影評論協會》,http://www.hermanyau.com/cnight5-1.htm
李曉明(
李黛顰,〈什麼是後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現象〉,《台灣文化研究網站》,http://www.srcs.nctu.edu.tw/taiwanlit/issue4/4-1.htm#title(
明報(
胡紹嘉,〈因為我會怕黑-談靈異節目的情感影響與閱聽反應〉,《媒體識讀教育月刊第12期》,http://www.tvcr.org.tw/life/media/media12.htm(2004/07/15)
陶東風(
麥香紅茶(
陳明輝(
謝鴻均(
雙瞳電影宣傳網(2002),《KingNet電影台》,http://movie.kingnet.com.tw/channelk/doublevision/
中文報紙
林美璱(2004/07/13),〈夏威夷買屋 田麗賺到好萊塢〉,《中國時報》D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