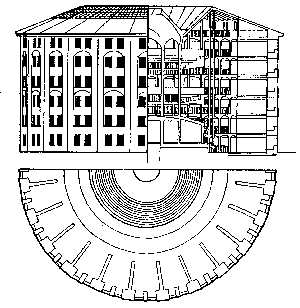
躲在衣櫃中的靈魂-從邊沁的全景敞視理論談台灣女同志的性與自我認同
林宛蓉(南華大學應用社會系四年級)
目
次
摘要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對象
第二節
分析方法
第三節
研究限制
第四章
全景敞視模型之論述
第一節
邊沁的全景敞視建築模型
第二節
規訓機制
第五章
台灣女同志之處遇分析
第一節
雙全景敞視模型
第二節
女同志的性與認同發展困境
第三節
女同志的反動侷限
第六章
結語
參考資料
摘
要
台灣女同志這個主體在同志運動歷程中一直都是隱而不彰,同時,台灣女同志的認同建構與情慾開展歷程也常常顯得比男同志壓抑與退縮。是什麼樣的原因讓女同志們在嘗試破繭而出的過程裡必須承受比男同志更大的壓力宰制,便是本文冀求探討的問題。
因此,本文採用文獻資料分析的方式,以邊沁的全景敞視建築模型作為基礎,來構築出台灣女同志在性與認同的形構過程裡,背後所蘊藏的權力運作機制。而從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女同志的生命景觀比男同志來得壓抑與逃避,在於女同志除了必須承受異性戀霸權所帶來的同志污名外,尚需背負父權給予「女性」這個主體的情慾壓制與控制。這使得女同志落入雙重弱勢的窘境,因而讓女同志在面臨自身的同志身分和情慾時,得承受比男同志更巨大的壓力與自我質疑的困頓。所以,如何鬆解異性戀霸權與父權在女同志身上的強大馴服作用,是女同志在建立性與自我認同過程裡相當重要的關鍵。
關鍵字:全景敞視建築、規訓、污名化、去性化、認同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社會環境迅速變遷,使得現代人生活空間呈現複雜及多元的景況,加以傳播媒體的大量興起與精進,資訊的流動比以往獲得更大的傳輸空間與曝光機率,許多訊息及議題因著此趨勢而不斷地被提出與討論。其中,「同性戀」的議題,不僅引起社會的強烈關注與激烈爭辯,更在經歷如此長時間的論辯與關切下,依然絲毫不減其熱度。這樣特殊的情形,不禁令人興起高度的好奇心。
察觀各種典型社會,我們會驚異地發現,「同性戀」的現象存在,幾乎是一種共通的文化特色與表徵。李銀河在其所著之「同性戀亞文化」一書中便有這樣的一段話:「同性戀現象是在人類歷史上,在各個文化當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基本行為模式,無論是在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還是在茹毛飲血的原始部落;無論是在20世紀90年代的今天,還是在遠古時代。」[1]
然而,在面對「同性戀」這樣一個普遍慣常的存在現實時,許多社會卻對其採取排斥與封鎖的行動。「同性戀」這個名詞被冠上了「不道德」、「骯髒」等象徵符號,在醫學領域中,同性戀則一直被看做「性別認同障礙」、「性倒錯」,役男體檢時,就把同性戀歸為「性心理異常」、「性心理變態」。[2]此外,大眾傳播媒體對同性戀的討論與塑造,往往也表現出扭曲性的負面報導。「同性戀」與「AIDS」兩者之間更是被劃上了齊等線。
當社會運用各種方式,想盡辦法將同性戀者關鎖入櫃的同時,面臨這般「同志污名化」困境的同性戀者,被迫退至社會的邊緣角落,而形成一隱匿的個體。在英美的俚語中,將同性戀者形容是「躲在衣櫃中」(in
the closet),真可謂是對同性戀者處境的傳神比喻。
只是,這樣的封殺效果,抹煞了我們對於「同性戀」的該有認知與了解,也因此,造成我們不是對其經常視而不見,不然便是產生誤解,甚至是恐懼。可喜的是,隨著同志論述的興起與同志運動的產生與努力,同性戀者逐漸為自己找到一種發聲的管道,而得以積極爭取自身的生存空間與權利。
同志空間與議題的開展與建構,使得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圖像重新形塑,而有較全面的世界觀之思考與認識,同時,也驅使許多研究者投入探究同性戀現象的行列中,因為「同性戀是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它的外延清晰,內涵獨特;同性戀作為一種亞文化(subculture)有著他獨特的游離於主流文化的特徵;同性戀者作為一個亞文化群體,具有獨特的行為規範和方式,是一個理想的研究課題。」[3]
而在描繪同志圖像的過程中,我們察覺到,在同性戀者生存困境的背後,有一套特殊的權力機制模型在其中運作。這套特殊的權力機制模型為何?它是如何運作?它對同性戀者在建立其性與自我認同的過程中產生何種影響或困境?同性戀者如何反抗或馴服於此套權力機制?便成為此篇研究亟欲探討的重點。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相關同志議題的探究與討論,隨著同志運動的開展與同志理論的發展,漸次的搬上檯面,加以大眾傳播媒體的蓬勃,同志們得以擁有更多的發聲與發抒管道,讓更多人了解及注意到同志這個邊緣群體,以期獲得更多善意的回應及看待。
因此,當我們走訪坊間書局,我們可以發覺到開始有相當豐富的同志議題書籍獲允在以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中登堂上架,其中蘊含許多同志自身的生命故事紀實與告白。電影、紀錄片、舞台劇、電視劇…等,也逐漸有越來越多相關的同志展演主題,甚至還有專門為同志朋友們所舉辦的活動,如「台北同玩節」,以及專賣同志書籍、VCD、CD…等同志相關消費物品的「晶晶書庫」。此外,同志議題也吸引相當多研究者投入,使得同志話題進入學術領域的討論,並有相當可觀的分析研究成果。這些發展,都使得同性戀者逐漸建立起豐富的資源網絡與獲得生存空間的延展、擴張。
綜觀這些資訊,我們可以發現到,許多的同志論題中心多半集中於探觀同性戀者的生存的處境與困頓及同性戀者性與自我認同的建構歷程。從這些討論中,我們了解到同志們的生命景觀狀態,也可以清楚察知在其生命景況形成的背後,隱藏著一組權力的控制機制網絡,宰制和影響同性戀者生存空間與生命景況的走向與發展。為了讓這權力機制模型清晰的呈現,以瞭解其施力的方式,所以,我嘗試運用邊沁的權力運作之空間模型-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來探究與建構蘊藏在同志生命圖像背後的那座權力機制模型,以便能更清楚掌握影響同志們在建築自身性與自我認同輪廓時的運作動力。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關於同性戀的定義與討論向來有許多爭議,而這些爭議點主要來自兩個觀點上的歧異,一個為本質論,另一則為建構論。以本質論來說,「『性取向』是跨越文化時空的客觀事實,是非此即比的性核心本質,獨立於文化論述而存在的客觀內涵。」[4]因此,對本質論者來說,同性戀是一種固定的性慾取向,它是一種「特定的存在與行為、慾望模式,不會因時、因地、因文化,以及其他差異因素(如年齡、個性、階級、種族、性別特質等)而有極大的不同。」[5]而建構論者則反對本質論的看法-同性戀是一種恆常的狀態,他們強調的是「同志身分的建構乃隨歷史變遷、地域文化而有不同。」[6]他們認為,對於同志身分的認同是經由與社會互動的過程中建構出來的,而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質存在。
因此,「許多抱持建構論的研究者認為,探討同性戀的定義與成因根本是問錯了問題,因為同性戀如果不是一個本質的話,何來定義與成因呢?每個人可以用不同的觀點來建構自己的性認同,每個人的性認同內涵可能都是不一樣的,其建構歷程也是不一樣的,所以瞭解同性戀之性認同的內涵與歷程比瞭解同性戀的定義與成因重要的多。」[7]因此,自一九六○年代建構論的提出與發展之後,「同性戀認同」的議題研究逐漸成為熱門主題,成為一門顯學。
於是,在建構論的基礎上所發展出來的同性戀認同理論,相當程度上強調了社會文化脈絡對於個人性認同形成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看見,在這樣觀點下的所展示的同志認同理論,大部分皆包含了兩項基本假設:「(1)認同是透過一個發展的歷程而獲得的(2)此認同的維持與改變乃是個人與環境互動下所發生的」。[8]在許多研究者所提出的認同發展理論裡,我們便都可以覺察到這種「階段性」發展的論述脈絡,如:Cass提出的同性戀認同形成的六大階段。
以台灣相關的同志認同研究而言,同性戀認同的論述,多半也是以社會建構理論為主軸,例如:鄭美里的「台灣女同志的性、性別與家庭」、劉安真的「『女同志』性認同形成歷程與污名處理之分析研究」、洪雅琴的「女同性戀者的自我認同分析」、陳麗如的「她們的故事:七個女同志的認同歷程」…等。但是這些研究論述,雖然強調社會文化脈絡對於女同志認同的影響,但是大多數還是偏重以描述女同志內心的認同心理過程為分析的主要重點,而未能說明這些社會文化脈絡是如何、以何種形式來影響女同志認同形構的歷程。因此,在本文裡,我將以社會建構論作為論述基點,嘗試以邊沁的全景敞視建築模型來說明社會文化脈絡影響女同志性與自我認同的情形。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對象
同志論題的討論,應該是一種跨性別式的研究取向,以避免陷入過去性別二分法之困窘。
然而,察觀過去的同志論述之建立,往往是以男同志作為一種論點建構的主體,而忽略了女同志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與生命歷程,甚至有許多關於同志的定義往往也將女同志屏除於外,因而使得整個同志研究發展造成偏頗之情況。
此外,由於台灣女同志所經歷的探索與壓迫過程,相當程度因為文化上的差異,也與現今發展而起的女同志相關研究有程度上的差異。因此,本研究借助過去關於性別的分類方式,選擇以女同志作為研究對象,以利突顯過往經常忽略的女同志主體,期使在過去同質性的理論基點外,重新審視台灣女同志不同於男同志的認同歷程,同時,進一步建構起台灣女同志自屬於己的權力壓迫論證模型。
第二節
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取文獻資料分析法以及文本分析作為此文之研究分析方法。因為,鑒於同性戀群體的特殊性、隱匿性,以及研究時程的侷限,所造成資料收集與分析上的不便,故此研究採取以邊沁(Bentham)的「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之模型作為研究的理論模型雛體,並藉由文獻資料與文本作為進行理論模型建構之資料來源,來作為此篇文章論述的方式。
本文中所引用之文獻資料包含已出版的同志論述書籍,中文的報章雜誌,以及相關同志研究之碩博士論文;文本資料則以相關同志主題的文字書寫及小說為主要的資料取向。另外還有相關同志電影的評述與討論及網路資訊,則作為研究分析資料的輔佐性資源。
藉由以上次級資料的收集與分析,研究者試著從中抽離出台灣女同志特殊的壓迫景況與認同建立過程,進而建構出台灣女同志背後的所蘊藏之全景敞視模型的輪廓,而這樣的方式也讓複雜的權力運作脈絡在分析上顯得容易許多。因此,借助現有之研究資料與文本,建立、描繪出台灣女同志生命景觀歷程背後的全景模型之概觀,是本研究選擇採用次級資料分析作為研究方式最主要的原因。
第三節研究限制
本文以邊沁的全景敞視理論作為論述的主要觀點,來討論說明台灣女同志在建構性與自我認同時,如何受到全景模型的影響。本文章利用全景模型當作研究的骨架,以文獻資料為內容分析之來源,嘗試建立一種概括式觀點分析的台灣女同志認同研究。
因此,這篇文章只利用文獻資料的分析,而非田野調查式的資料解析,當然,在這種方式下,對於女同志的個別差異,如社會階層、學歷、年齡,並無法有太多的著眼和比較。所以,這篇文章的論述裡,是無法清楚呈現出女同志之間的差異性是否會讓全景敞視權力的運作模型產生不一樣的程度效應。而這部分將留待以後再進行更深入的分析研究探討。
第四章
全景敞視模型之論述
第一節
邊沁的全景敞視建築模型
一七八九年,邊沁(Jeremy
Bentham)提出一種新的監獄建築型式概念,這個建築模式是一種圓環型構造設計。依據邊沁的建構想法,此圓環型監獄的建築基本原理為(見圖一):
四周是一個環型建築,中心是一座瞭望塔樓。瞭望塔樓有一圈大窗戶,對著環型建築。環型建築被分成許多小囚室,每個囚室都貫穿建築物的橫切面。各囚室都有兩個窗戶,一個對著裡面,與塔的窗戶相對,另一個對著外面,能使光亮從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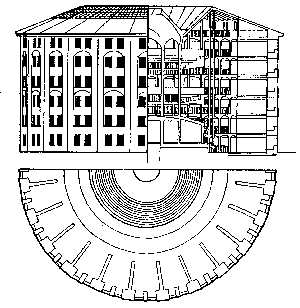
圖一
The Panopticon of Jeremy Bentham[10]
在這樣的建築空間設計中,空間的逆光效果是一大特色。這使得每間牢房儼然像個小舞台、展演台,每個囚禁者成為舞台上的演員,清楚的、透明的為中央塔台的監督者所觀看,卻無法觀看到瞭望塔中的情況。「這樣的可見性之特色,顛覆了過去監獄的建構原則-封閉、剝奪光線和隱藏。它只保留了第一個功能,消除了另外兩個功能」,[11]因為,充足的光線照明效果比起黑暗的隱藏效果來說,更能使監督者更有效的觀察囚禁者的一舉一動。因此,邊沁的此種圓形監獄建築設計,被稱之為「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座圓形的全景式建築是「一種分解觀看/被觀看二元統一體的機制。在環形邊緣,人徹底被觀看,但不能觀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觀看一切,但不會被觀看到。」[12]這樣的機制產生了一種持續與強大的監視與規訓的效果。因為,囚牢的設計是面對著中央的瞭望塔,這讓被囚禁者感受到自己遭受監視的現實,但由於無法確知監視者是否在塔內,或何時受到窺視,因此,被囚禁者必須將監控視為一種恆常性的行動,而隨時注意自身的行為舉動。
這樣的權力效應,使得被囚禁者變成自己的監視者,因此,不管中心瞭望塔的監督者是誰,或者有無人來行使監督權力也就不是那麼重要了。當然,無論監察者是基於何種動機或心態,是好奇心驅使,是窺視慾…等,這個圓形建築也依然不受影響而能產生同樣的權力效應。
這是一種重要的機制,「因為它使權力自動化和非個性化,權力不在體現於某個人身上,而是體現在對於肉體、平面、光線、關注的某種統一分配上,體現在一種安排上。這種安排的內在機制能夠產生制約每個人的關係」,[13]這般權力的壓制與體現是直接而自動的加諸在受制者本身,這讓權力的使用更為輕便與有效率。
此外,全景敞視建築也是一間實驗室,它可以對受囚者進行一連串的試驗、評估與分類,甚至是行為改造及規訓。且在這個全景敞視建築模型裡,還包含著一個監督自身的機制結構,而這樣的機制讓監督者在監視與規訓的權力機制運作過程中,無可避免也會被捲入這個機制裡,正如邊沁所說的:「由於我設計了各種聯繫紐帶,我自己的命運也被我栓在這些紐帶上。」[14]
這種機制的存在,讓權力成為了雙面利刃,如同Gwendolyn
Wright and Paul Rabinow在“Spatialization
of Power:A Discussion of the Work of Michel Foucault”一文中所引用的一段話:「這可能是這種意念及其引出之各種運用的最殘酷的一面。在這個管理的形式中,沒有一種單獨個人可以完全擁有、操弄而加諸他人的權力,在這個機器中,每一個人都被網羅,不管是權力執行者,或是受制者都一樣。」[15]
對邊沁而言,全景敞視建築不僅是個透明的鐵牢籠,也是個完美的規訓機構模型,它更是權力的運用達到一種完善境界的體現。它採取一種精神對精神的權力運作方式,使得權力的行使更為經濟且有效率。同時,全景敞視模式的使用,讓權力的施展不再只是僵硬笨重的壓制手段,它將權力轉化並滲透於各種職能中,如生產、教育、懲罰、醫療…等,使其體現於各種職能裡,而強化了這些職能的效用。它讓所有使用它的機構產生最強大的力量,而這些能量只需要靠一個簡單的建築學與幾何學設計,即可達成。
第二節
規訓機制
古典主義時期,君王被視為是權力的中心象徵,任何的犯罪行為都成了侵犯君權的舉動。為了確立君主權威,於是舉行公開的懲罰儀式來處決犯罪者,而這些刑罰的方式,皆包含了對肉體的殘酷拷行。這樣的公開酷刑,隨著啟蒙時代的來臨,天賦人權、社會契約論..等論述的提出,被批評為相當不人道的方式,而逐漸出現改革的聲音。因此,肉體的酷刑被取消了,取而代之是一種新的懲罰形式-監獄,一種被視作具人道的處罰機制。
只是,以傅柯的關於權力的論述來看,這些在傳統歷史論述下,所闡明的「事實」,如:「公開的處決儀式修補了君主的權力」、「社會改革的動力來自於天賦人權等觀念的提出」,其實蘊含著一種權力運作轉變的意涵,這樣的想法我們可以從以下的一小段文章中看出端倪:
當君主對犯罪者施加某種力量(如肉體酷刑)時,藉由公開的儀式,在觀看的群眾間形成了對君王權力的感知與談論,因而產生了對君權的論述。另一方面,在公開的儀式中,群眾除了在恐怖的情景中感受令人生畏的無上君權外,也產生了複雜的情緒,不管是集體鼓譟叫好還是怒罵,或者不滿處決過程或藉著人多鬧事,都嚴重傷害到君權的莊嚴,[16]甚至影響到這場修補君權的儀式完成。
由此可知,古典時期,當君權施加於臣民時,同樣也會伴隨著同等力量的反撲,這使得此種由上對下的權力機制運作顯得相當的不穩定且充滿變數。因此,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出現改革的聲音與冀求。然而,改革的目的並非如傳統歷史論述所顯示的,是為了所謂人權或者人道的考量,主要的目的其實是在於尋求一套完美的權力運作機制系統-均勻而不間斷的施力卻又不會有反作用力。[17]
因此,從公開的酷刑到監獄產生的這段歷史變遷,若從傅柯的觀點來看,其代表的並不是一種進步的結果,而是一種權力運作機制的轉變過程罷了。這轉遷的歷程在於,「古典時期的權力機制,是單純的兩個力量的拉扯,一個是君王,另一個則是臣民。當君王將權力施加於臣民身上時,臣民自然會反饋一股反作用的力量回去。」[18]然而,現代的權力機制就顯得繁複許多了。現代的權力機制主要是利用「微觀權力」的施展,來達到其控制的目的。它將權力轉換為各種意識型態或知識,並將其滲透、深入到個人機體裡,而影響著個體的各項行動,甚至是思考模式。簡單來說,現代的權力機制其實是運用各種方法、訓練,對人體以一種支配的力量,達成全面性、持續性的監控與征服,而這些方法、訓練,我們則將之稱為「規訓」。
規訓,「規定了某種對人體的具體的政治干預模式,一種新的權力『微觀物理學』,一種有關細節的政治解剖學。這種政治解剖學以人體為對象,細密的將人體分割為各部分,將每一部份視為政治權力的施力對象,以便得到最大的功率。」[19]這種規訓機制的運用,是將權力移轉轉至日常生活中運作,而深化至個體之中。這種權力行使的轉移最大的效用在於它讓權力以最低的代價,實行監控個體目的,同時,也不用擔心權力施展後,產生反力。此外,在規訓的機制裡,為了讓權力更有效發揮作用,「所有的權威根據雙重模式而執行著個別控制的功能,即二元劃分和貼標籤的功能(瘋癲/健全、危險/無害、正常/異常),以及壓制性的指派和差異化的分割之功能(他是誰、他必須在哪裡、他如何被刻劃、他如何被確認、如何以個別化的方式在他身上執行一個恆常性的監視,等等)。」[20]規訓,將人帶進一種精細的分析與分配空間中,以讓權力的施展細緻的滲透入個體各層面,而使個體徹底籠罩在監控中,進而達到馴化的效果。這是現代權力運作機制最重要也是最終的目的。
邊沁的全景敞視建築模型,為這個現代的權力運作技術,提供了一個理想完美的圖像與施行軌道。在這個權力的烏托邦裡,權力可以不斷的向某個點施力,不過受力者卻無從得之施力的來源,這會使得受力者持續地將自身籠罩在規訓的機制陰影裡。這是一個完美的權力運行方案,它使權力的行使變的輕便且能有效的深入每個受力者的行為。而這種的新權力學的巧妙設計,更為規訓機制擴散至社會機體裡,確立了一種普遍化的模式,因為,「它編制了一個被規訓機制徹底滲透的社會在一種易於轉換的基礎機制層次上的基本運作程序。」[21]因此,當社會在逐步規訓化的同時,整個社會機體也愈像是一個全景敞視建築了,而生存在社會機體的每個人,則在權力規訓無所不在的監控、塑造下,成為「柔順的人」。
第五章
台灣女同志之處遇分析
綜觀上章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全景模型是一種特殊的權力運作邏輯設計,它讓權力成為一種隱微的力量,得以內化至個體之中,而不容易察覺。這樣的權力施展不僅減低了權力反撲的風險,同時也可以使權力在最經濟的情況下發揮最強大的作用。而在同志的身上,我們便發現到這種全景模型的實踐與作用。因此,以下,我們將就全景模型如何在同志身上施用,且對同志造成何種影響來作進一步的討論與分析。
第一節
雙全景敞視模型
一、
異性戀霸權
「同性相斥,異性相吸」是一個自然的物理定律,同時,也被當成人類情感關係的一項圭臬。從出生開始,我們所接觸到的、學習到的就是這套律法,也習以為常,終而將之視為「理所當然」。
人對世界的認識,始於家庭。在出生的那刻起,我們見到的便是「異性連結」的組合。對「家庭」的解讀,也總包含著一男一女所組成的最基本礎石。於是,每當老師要求自我介紹時,最常聽見的一句話即是:「我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在這介紹詞裡,其實,強烈表徵出的是一個「異性戀觀」認知,因為,這裡的爸爸、媽媽,所代表的是一個男生(爸爸)、一個女生(媽媽)的必然想法,而不會是兩個男生,或者兩個女生。
在學校裡,我們總會聽見調皮的小朋友喊著「男生愛女生…」,卻不曾聽聞「女生愛女生;男生愛男生」的話語出現;課堂上,老師上的「兩性關係」,所有的話題皆以「男女」建構出來的關係作為討論的中心,如男女的相處之道,男女的情感處理問題…等,卻不會討論男男、女女的相處方式,情感處理的方式;校規裡,規定的是「男女生不得談戀愛」,而不會是「男生與男生不得談戀愛;女生與女生不得談戀愛」。在這個空間裡,我們學習到的,只是以男女之相異體所建立出來的情感關係常模。
社會中,聽聞的各項影像,接受的各種媒介,也多半是強調異性情感的模式。電視劇裡描繪的劇情總脫離不了男女主角的感情戲碼;流行音樂唱的說的是男女情感的悲歡離合;電影裡的浪漫愛情戲,談的也是一男一女的感情互動;漫畫、小說、文學作品、童話,故事寫的也會是「王子與公主」,而不會有「兩個王子或兩個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甚至是新聞上的報導、周刊上的緋聞八卦,充斥的依然也只是男與女的情事轉折。
我們在建構的世界,是一幅填滿異性戀觀的社會圖像。在這個以異性戀觀為主流的社會裡,同性戀者的存在,形成了一股挑戰的力量,因此,為了讓異性戀觀穩住其主導地位,於是利用相當多污名化的動作與生活限制,將同性戀者打壓至低劣的地位,以維持其正當性。
以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得知,當逐步建立起異性戀知識的同時,異性戀機制便開始建築屬於自己的權力架構,而污名化同性戀更是在建構與穩固此權力機構時重要的基礎。
對於同性戀,異性戀機制賦予他們許多的符號,例如:娘娘腔、男人婆、性倒錯、性別認同障礙、性心理異常、性心理變態、骯髒、不道德…等,最後更與愛滋病(A.I.D.S)劃上齊等線。這些符號的使用,讓同性戀者貼上了病態的標籤,而被劃歸至變態、異常之列,其最終的目的在於突顯異性戀的正常與自然,而使得異性戀觀更加鞏固。
分類的污名,使得同性戀者被迫披上罪惡的外衣,成為眾之矢的。同時,在此分類污名之影響下,大眾產生對同性戀者的嚴重偏見與歧視,不僅形成一片「同性戀恐懼症」之氛圍,更激烈的,還有暴力行為的發生。例如:某父親發現女兒為同性戀,憤而動手教訓女兒[22];學校以及民間的輔導系統,在面對同性戀者時,將之界定於「性心理異常」,而企圖以各種方式「矯正」之;監獄中如發現了同性戀情事的發生,將會對同性戀者採取嚴厲的懲罰,並且立刻調房處理。這些例子,都只是鳳毛麟角罷了,異性戀還以更多的方式監控、限制著同性戀者的一舉一動,一旦發現其行為「踰矩」,便採取「消滅」動作。因此,在這種情形下,同性戀者只好將自己偽裝成異性戀的模樣,以避免受到不善意的眼光與傷害。
此外,雖然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同性戀的可見度大增,然而同志污名的程度卻非但沒有減輕,反而有強化的現象。這從以下的一段文章陳述中即可看出端倪:
就同志處在於一個社會弱勢族群的角度而言,媒體的高曝光率確實增加了同志的可見性,這也是目前台灣同志運動的策略,因為唯有引起媒體的注意,才能爭取到發言權,也才能影響到報導對於同性戀形象的呈現。然而,可見度的增加同志是否真的就從媒體上取得了主體性?這確實是值得深思的。若進一步檢視媒體對同志新聞的報導內容,除了同志運動策略性包裝的訴求較能引起媒體正面報導外,在其他方面的報導上不難看出媒體依然是充滿著偷窺獵奇的心態,或者以衛道之姿捍衛既定體制,而對同性戀加以污名化,同志依舊處於一個邊緣的位置。除此,我們也可以發現媒體似乎也喜於把同志當成一個〝標籤〞,四處與各種議題連結來創造另一種〝新聞價值〞或說是增加新聞聳動性。就這個思考點而言,媒體對於同志議題的〝關注〞,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把同志議題當成一種異性戀議題過度曝光後的調情作用罷了。[23]
另一方面,由於對同性戀所知甚少,因此人們通常都藉由媒體所傳達的訊息來描繪、建構同性戀的圖像和認識。所以,當媒體對於同性戀的報導以扭曲、污名化的方式呈現時,也將造成社會大眾對同性戀的負面評價、形塑,甚至是恐懼。由此我們可以得知,媒體不僅沒有鬆綁了異性戀機制對同性戀的束縛與宰制,反而還成了鞏固異性戀權力機制的重要幫兇。
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知道,異性戀權力模型透過各種機制,如污名化、媒體再現、教育…等,將異性戀觀之意識型態細微的施展內化到每個人身上,使所有人皆規訓在異性戀的權力之下,「異性戀」成為社會個體行為的圭臬,同時,每個人也會將它視為審查他人的標準。因此,任何違逆的力量將受到嚴厲的「責罰」對待,如同性戀便是「罪惡」、「偏差行為」,人皆撻伐之並該將其引導至「正途」。
在這套異性戀全景敞視機制下,每個人都是行為的「監督者」,仔仔細細的巡查「錯誤」,因而身為同性戀者,則必須盡力去隱藏身分,小心翼翼的偽裝好自己,否則一旦被發現行跡,將遭致「懲罰」。
無怪乎,張娟芬在「姊妹戲牆-女同志運動學」一書中,要將此異性戀全景敞視機制形容為「異性戀霸權」。
二、
父權
父權簡單的來說,是一套男性壓迫女性的權力機制。在父權體制之下,女性的生存價值依附於男性而生,形成「男尊女卑」的社會定律,縱使在今日,強調男女平等的現代社會,父權仍然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力量,緊緊的攀附住女性。
在父權的價值裡,男性將女性視為生育的工具,女性的價值僅在於「傳宗接代」的能力,除此之外女性是不具任何個體價值的,她只是為男性所擁有的一項物品,是男性的「私有財產」,為其所有且受其控制。而女性既然是男性的私有財產,因此「女性」對男性而言即存在著獨占性與不容侵犯的意義,而為了保護、宣示此私有財產的所有權享有,男性便定出了相當多的規範、倫理道德,以來控制、保障「女性」這個私有財產的獨有性。
「貞操」觀念是其中影響及壓抑女性最為徹底的一個規制,也是讓女性私有化更為彰顯的手段。我們可以在許多中國故事或戲劇裡發現一些這樣的事例,例如:女人必須在新婚當夜,於行房時落紅,以證明其「清白」,是「完整」的為其丈夫所有,否則將為丈夫所怨恨,甚至休離;「貞節牌坊」是女性最高的榮譽象徵,當然也是女性的行為準則。它牽制著女性在喪失丈夫之依附體後,尚必須保留自己以完整地屬於那個已然消逝的個體。如有不貞的情事發生,通常都會遭受嚴厲的懲罰,如:「浸豬籠」。[24]而不管是哪個例子,我們都可以發現到一點,女性在父權權力的施展、監控之下,她變成一個「去性化」的個體,她必須將自身的情慾抑制,不得任意宣洩。這從中國語詞的使用上便可得知:當一個男人放縱情慾時,我們稱之為「風流」;而當女人放恣情慾時,則視之為「淫蕩」,加以撻伐之。
另一方面,父權除了將女性「去性化」之外,也驅使女性「弱勢化」、「次級化」。之前我們曾提到,女性在父權系統下,是被私有化的。在這樣的一個設定下,男性是關係的中心,女性僅被當成是一個客體,而非主體,其伴隨男性這個主體而存在,同時也為其所掌控。
因此,在家庭的關係主軸裡,女性被設定為「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扣緊此「三從」標準,女性被定位於一種輔佐性的角色,她不具有任何主導性的價值,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常會聽到「女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丈夫是天」的話語出現。這樣「重男輕女」的導向,造成女性在資源上的獲得缺乏與艱難,同時女性也是一個不具備隱私權的受侵犯個體,因為在父系家庭體制裡,女性必須承受嚴密的監控與性別規馴;在工作場域裡,以男為尊的系統,也使得女性在能力與工作競爭上,備受質疑、歧視與壓迫。例如:男性的升遷總比女性來的順利與快速;在公司裡,女性主管比例遠低於男性主管,政府部門亦是;男女性工作者的「同工不同酬」;「單身條款」、「禁孕條款」…等。這種種的限制,往往使得女性在工作空間的伸展上阻礙重重。拿最近相當轟動的「中華開發代理董事長」一事來說,其中的父權意識表露無疑。
當陳敏薰以「中華開發代理董事長」之身分登上商場舞台時,迅速的引起媒體與社會的廣大關注與討論。而激起如此熱烈討論的,並不是因為她卓然的工作才能與表現,而是在於她那被喻為「媲美蕭薔」的美麗容貌,以及顯赫家世的背景,還有那帶點神秘色彩的感情生活。從電視媒體到平面的報章雜誌,所有的焦點都集中在對其的「品頭論足」上,包含她的服裝、容貌、家庭背景、男友身分,在這當中,我們可以發現,當陳敏薰以女性之姿躍上檯面後,便無可避免的陷入男性主觀的價值體系中。任何有關陳敏薰的報導都存在著男性觀點的觀察-美貌、身家背景、情感狀況,而這些觀察的評價中,在在都可以嗅出某種訊息-陳敏薰有今天的地位,其背後的支撐是來自男性的庇祐與給予。這樣父權式的論述,讓陳敏薰本身的才能表現被淡化,甚至是忽視了。
時至今日,兩性平等的口號喊的甚囂塵上,女性主義者也大張旗鼓的宣揚對抗父權壓迫的決心,在一片的喧揚中,我們以為看見了一些改變。然而,「對兩性平等關係抱持憧憬理想的行動,它到底是一種消解歷史上所沉澱豐富以父權中心的底層意識;還是,文明社會越趨開放、進步,就好像我們在消費市場上,可以比以往得到更多物質性的消費形式一樣,卻誤以為我們在兩性關係上得到更多元的實質內容?如果是後者,那它是因為現今的開放性環境所促使如此般『空間』所形成的時代性產物,它也許是政治的、經濟的、商業的、流行話語的『空間』,而不是真正在兩性關係的深層脈絡上改變了什麼?」[25]我想,我是同意後者的,因為,我們可以發現,表面上,我們似乎爭取到兩性關係上的平衡,但在本質上父權意識依然穩固的位居社會主體位置。例如:女性美容、整容的消費大行其道,深究其因,全因父權意識作祟;受暴婦女雖然得到律法上的保護,可是精神上依然承受相當龐大的壓力,不管是擺脫不掉的父權意識-女性貞潔作祟,還是來自各方的歧視性眼光。
綜合以上來說,我們可以看到,父權就像是一座全景敞視式監牢,它透過各種媒介(如媒體、家庭、學校)的影響與深化,將權力的施展解化以一種無知覺的、自然的方式(如倫理道德意識的灌輸),介入位居其中的受囚者行為中,而不為其所發覺。它馴化、控制置身其中的每個人以父權之價值體系,尤其是女人,而對於同樣身為「女性」的女同志而言,父權全景機制的監控一樣也影響了女同志這個主體,使其在異性戀全景機制的壓迫下,必須面臨另一層的壓抑。
第二節
女同志的性與自我認同發展困境
張小虹在《姊妹戲牆-女同志運動學》一書中作過這樣的比喻:「如果說異性戀霸權是個衣櫃的話,那麼它大概是有分『男櫃』與『女櫃』的,可以說是「一國兩制」。男櫃較大,在背面靠牆處有透氣孔,以防櫃內悶熱或有異味;女櫃則密不透風,衣櫃裡還有層層疊疊的隔間與抽屜。當我們形容同志的處境是『衣櫃處境』時,那麼女同志的處境也許應該形容成『抽屜處境』了。」[26]這種說法,為女同志所遭受的雙全景機制壓迫現實作了一個相當貼切的詮釋。
對女同志而言,異性戀霸權和父權是一組不可分割、相互作用的全景權力機制模型,置身其中的同女,不僅必須承受異性戀霸權所帶來的歧視與壓迫,同時更需要面對父權所附加的鎖鏈束縛。而在異性戀霸權與父權雙重壓制系統下,女同志不但得面臨雙重弱勢的窘境,更須承受較男同志多的壓力和約制,也因此,女同志在構築自我的認同上與情慾的抒發上,經歷了比男同志更多的矛盾、挫折、壓抑、不安。
一、
女同志的自我認同:
在回溯與整理女同志自我認同過程裡,我們會發現:「通常除了在特定的情境下-例如被詢問必須表態、為了作為區別,或為了性別政治身份的宣示-之外,日常詞彙中,很少人會直接說自己是『女同志』,而是說:『我喜歡女孩子』。」[27]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因為「同性戀」一詞所背負的強大社會污名。「然而,在異性戀機制的界定下,有同性愛慾的人被迫貼上同性戀標籤、接受同性戀身分,連帶而來的污名感更是同女生涯裡必須一再面對、處理的課題。因此,『反污名』就成了女同志實踐同女生涯、建立自我認同的重要生存鬥爭。」[28]
以多數女同志的情況來說,自身性意識的傾向與對同性情愛的自覺是早於「同性戀」這個概念的:
第一次發現自己喜歡女生,是在我國一的時候。那時候是因為有人喜歡我,我也沒有想過會是這樣子的關係。當時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覺得喜歡就喜歡吧,沒有任何其他感受,就是喜歡而已。[29]
發現自己喜歡女生,是高一,我想這個跟環境有關。國小和國中的時候,覺得自己比較喜歡女孩子,當時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只覺得自己蠻喜歡一個女孩子而已。[30]
原本我不知道同性戀是什麼、要幹什麼,只知道我喜歡她。[31]
由上面的陳述的我們可以了解,許多女同志在認同的初期,對於「同性戀」的概念是模糊的,甚至是沒有知覺。這種情形大概與異性戀機制對於女性同性情慾的「消毒」有關。在異性戀的場域裡,女性同性的情慾總是被形塑成「姊妹情誼」、「手帕之交」的所謂同性愛,而非所謂的「同性戀」,這樣的「同性愛」歸類,讓許多女同志在面臨「同性情慾」傾向時,往往也就視之當然了:「上了高中,學校裡的老師、同學,都十分支持女人之間的情誼,自然而然,大家的感情就很好,也沒有什麼好特別奇怪的。」[32]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女同志本身是很難建立起對「同性戀」這個主體的身分認同。
而隨著自我的摸索以及接觸後,同女們漸漸開始意識到自己與其他人有所不同,「同性戀」的概念漸漸出現,但也在同時,污名化的同性戀標籤伴隨而來,造成女同志在自我的本體認同建構歷程上增加許多不安與阻礙,這從以下幾段同女們的自白可以窺見:
當我發現自己原來喜歡的是女人時,曾經很不好受,那些社會的眼光,既定的道德規範,對我造成很大的壓力,甚至使我對自己產生挫折和懷疑。[33]
我在國中時代就已接觸同性戀,在高中時期有同性戀行為;那時候,我有一個十分要好的同學,可是我會不斷第給自己找很多藉口,例如好朋友啦什麼的去解釋它。而且不知道為什麼,只要聽到「同性戀」三個字,我就會覺得很不舒服,如果班上有人在討論同性戀話題,我就會禁不住想:她們是不是在說我啊?[34]
第一次聽到同性戀應該是國中的時候,大概國二吧!班上那時候除了我之外,另外一個女生也是常常會被女生包圍,有一些比較早熟的女生就會說你們這個樣子叫做「同性戀」,那時候覺得自己有點怪怪的。一般來說,社會的狀況就是男生跟女生,為什麼我不喜歡男生,反而比較喜歡女生?所以在一些報章雜誌看到這些字眼,會特別去留意。那時候,雜誌的報導和說法比較負面,讓我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可能是社會道德觀中所謂的異類,或者是那種不正常的一群人。[35]
我跟她已經有奇怪的事情發生。然後那時候開始覺得害怕,就開始覺得恐怖。就是,這樣不行。那時候開始知道,這樣不行,這樣好像是同性戀。[36]
這樣的不安與矛盾情慾,為女同志的認同之路增添許多壓力,而外界的歧視誤解與恐同情緒,無疑是雪上加霜,更讓女同志在自我認同的過程中承受強大的壓力與痛苦:
我開始喜歡一個女生,自己強烈感覺到對同性產生情愫,但我卻不敢去正視它,因為我從小生長在一個保守的家庭,父母都很排斥同性戀,所以我很痛苦,不敢將這件事告訴任何人,但我真的很喜歡她。[37]
那些男生在你心目中是很完美的典型,老師也很喜歡,‥就是他們平常什麼玩笑也不亂開,髒話什麼都沒有。可他就是可以看到兩個人比較親密,她就馬上蹦出那種很激憤的話。然後你就覺得,太可怕,‥你就知道同性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可以讓那種紳士完全沒有修養。[38]
在許多女同志的文字書寫裡,我們不難看見同女們在面對這樣內外壓迫時,對自身處境所產生的哀仇與絕望。她們利用文字刻劃下她們的生命告白,這其中意涵著一種深刻的挫敗與苦痛:
當人是很辛苦的,使我們覺得困難的,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挫折與壓力,而是在社會生存的本質就不適合我們,每日在生活上,都覺得不容易,而經常陷入無法自拔的自暴自棄境地。[39]
我以我赤裸之身做為人界所可接受最敗倫德性的底限。
在我之上,從黑暗到光亮,人慾縱橫,色相馳騁。
在我之下,除了深淵,還是深淵。
但既然我從來沒有相信過天堂,自然也不存在地獄。
是的在我之下,那不是魔界。那只是,只是永遠永遠無法測試的,深淵。[40]
我在這裡,我被世界徹徹底底推出來,我撞到「殘忍」的實體,我恍然明白,無論我心裡是怎麼樣的人,無論我此刻如何呼喊著要和小凡融在一起,無論我正如何因渴望著愛她而被壓垮,世界根本就不管我,不是由於現實條件或人與人無可奈何的對待。即使眼前這個女人親口告訴我也沒用。甚至沒有「不公平」或「道德」的問題,因為世界根本就沒有看到我。[41]
我突然覺得有千斤重的羞恥壓在我的唇上,這股附體般隨傳隨到的羞恥感,像是隱形緊箍著我的身體的皮衣,長久以來霸道地畫下我和別人的疆界…想到與皮衣間的掙扎,無限心酸。[42]
過去那個世界或許還是一樣的,從前你期待它不要破碎的地方它就是破碎了;但是世界並沒有錯,它還是繼續是那個世界,而且繼續破碎;世界並沒有錯,只是我受傷害了,我能真的消化我所受的傷害嗎?如果我消化不了,那傷害就會一直傷害我的生命。我的悲傷和我所受的傷害可以發洩出來,可以被安慰嗎?在我核心裡真的可以諒解生命而變得更堅強嗎?[43]
在上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從探索到掙扎、痛苦,甚至覺得羞恥的感知,一直深深盤據在許多同女的認同歷程裡,這是在異性戀霸權與父權的交替使力下,所加諸其身的社會道德倫理感作祟,在污名環繞的空間裡,她們漸漸的也產生了自我的污名感。這樣自卑無力的狀態,使得許多同女只好深深的將自己藏在不見天日衣櫃裡,來換取一點點的自我空間。這樣的窘境,讓女同志在建構起自我的「同性戀」的身分認同時,更是顯得困難與無助了。
二、
女同志的情慾世界:
在整個女同志的描繪與歷史建立上,幾乎很少把重點著墨於女同志的「性愛關係」之上。這是因為,「在異性戀霸權的窺視下,男同志一直被醜化成只會尋歡的性慾動物,與這個偏見平行的,是男同志豐富的性愛文化,從色情刊物、新公園、愛河、三溫暖,到警方不時破獲的男色應召站。同女的性事相對來說比較不被醜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女人作為性主體的能力與女女關係的深度,根本就不被社會所承認。」[44]
對異性戀者來說,「性行為」的概念是構築在「陰莖插入陰道」這個「插入」模式上,而以男同性戀者來說,雖然男同志的性行為當中並不完全具備了陰莖與陰道兩者,但以異性戀的性愛觀來說,男同志者擁有陰莖這個性愛的主體,而肛門、嘴皆可視作陰道的替代象徵,而可完成這個「陰莖插入陰道」的性愛模式,因此,男同性戀者的性愛是可以想像與理解的。然而,以女同性戀者來說,其並不具有性愛行為的主體「陰莖」,這使得女同志的性愛關係變得難以想像和認同,因此女同志的性愛關係很自然地便被否定與排除了。所以,在陽具中心觀的主導下,女同志很容易的便被歸類為「無性慾」者了。
除此之外,父權對於女人身體的掌控與規訓,使得女人對於「性」產生污名感,如:性是骯髒、不道德的,因此,女人對於「性」總有著相當的排拒與恐懼感,當然,更不用說有所謂「性愛的想像」了。
於是,同女之愛被放上了「無慾」的標籤,一種「春風蝴蝶式[45]」的愛戀。如黃碧雲的《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便是這樣一個春風蝴蝶式的愛戀故事:
或許因為大家都不肯道破,我與她從來沒有什麼接吻愛撫這回事,也沒有覺得有這需要-所謂女同性戀唉唉唧唧的互相擁吻,那是男人們想像出來攪奇觀,供他們眼目之娛的,我和之行就從沒有這樣。我甚至沒有對之行說過「我愛妳」。但此刻我知道,我是非常愛戀她的;愛戀到想發覺她有沒有性情氣質的地步。[46]
此外,「在幾個優秀的女同性戀小說裡,我們也都可以看到『同女無慾』的主題以各種變貌交替出現,如朱天心的《春風蝴蝶之事》、曹麗娟的《童女之舞》、王安憶的《弟兄們》等等。」[47]
然而,這種春風蝴蝶式情愛的塑造與父權對女性性主體的剝奪,卻使得許多女同志在面臨性慾的渴求時,顯現出疑惑、不安及恐懼,而造成對自身主體的焦慮與否定:
我是被命運責備過的人。
你看不出來嗎?我正在悔改。
如今,即使只是去吻一朵花,
我也會顯得十分鬼鬼祟祟了。[48]
一直到此刻我仍然不真的明瞭那種恐懼感,它到底來自哪裡?卻受著奇怪性慾的壓迫與恐嚇渡過青春期和大學時代的一半。[49]
成長的血肉是攪拌著恐懼的混泥土,從對根本自己和性慾的恐懼恐懼攪纏恐懼…,變成對整個活下去的恐懼怪獸,自覺必須穴居,以免在人前現出原形。[50]
綜合來說,異性戀霸權與父權造就了一個情慾控制的枷鎖,牢牢的銬著女同志的心緒。這樣的壓制與磨滅的殘酷,逼使女同志驚恐於一個自己都不了解的自身本體慾望,甚至害怕的驅逐、壓抑那股強烈的情慾熱流。
相對於男同志而言,異性戀霸權與父權這樣的雙重壓迫,使得台灣女同志在面對自己同性性慾的時候,往往顯得慌恐與無知,甚至選擇淡化處之,以所謂「春風蝴蝶」式的情愛自居。因此,對許多女同志來說,性與慾的舒展過程中,尚須面臨許多嘗試、摸索與勇氣,才有可能向前邁進,正視、接受來自自身渴望的要求。
第三節
女同志的反動侷限
伴隨同志團體的創立與同志運動的開展,同志得以獲得更多建立自我認同的資源與元素。對女同志而言,除了相關團體的支持性資源外,女性主義的興起也提供了相當多助力,其解構父權體制對女性本身的限制與監控的努力,對女同志在面對自身之身分認同與性慾的舒展,都提供了強化的力量。
過去的女同志者由於異性戀霸權與父權的雙重監控體制,使得女同志為保自身而須將自己隱匿,加上無法得到相同處境的同伴支持與扶助,許多女同志成了孤絕的個體,甚至有許多女同志投身異性戀的婚姻裡,以逃避同性戀污名所帶來的為難、痛苦處境。即使因為同性情慾的不受正面肯定而選擇不婚者,同樣也得承受單身所引帶而來的壓力。種種社會加諸女同志身上的壓迫,使得女同志在建構自己的身分認同、與情慾發抒上,面臨各種障礙與危機。
而隨著圈內空間的開展,女同志在面對自己的同性情慾時,不再是孤軍奮戰,其在圈內空間中得以獲得更多的情感寄託,同時,藉由與其他同伴的相處與凝聚,對其在自我的身分認同建立與強化及情慾解放來說,提供了正面的影響與助益。更有一些女同志除了消極的尋求認同支柱外,尚積極的擴展女同志的生存空間與企圖轉化自身的污名標籤,以期得到更多公平的對待。舉例來說,在校園中,有許多女同志社團的成立,如台灣大學女同性戀研究社(簡稱浪達社);在社會中,也有女同志社群的成立,如「我們之間」;在日益發展的網路空間裡,也有許多女同志的網站、BBS站。除此之外,還有專門提供同志相關資訊的書店-晶晶書庫。這些社群的出現,不僅給予女同志有更多的資源與空間,更讓異性戀霸權與父權掌握下的壓縮的女同空間與認同危機,產生與之對抗與扭轉的積極意義。
此外,許多文化式的展演也讓女同志得以用另一種形式來達到「發聲」的效果,如戲劇、文學、音樂…等。於是,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女同志電影、電視戲劇,例如:「美麗在唱歌」、「自梳」、「雙鐲」、「逆女」…等,也有許多女同志的書寫,如邱妙津的「鱷魚手記」、「蒙馬特遺書」;朱天心的「春風蝴蝶之事」;曹麗娟的「童女之舞」;杜修藍的「逆女」…等。
這些行動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為女同們開創了自我身分認同與情慾紓解的立基點與力量的強化,也讓同志運動的關懷面觀更為均衡及全面的關注到女同志這個主體。
只是,以台灣整個同志文化的展開來說,女同志這個主體經常會被有意無意的忽略了。例如:在同志運動的歷史中,我們都記得「新公園」這個場域所意涵的同志血淚史,不過,我們該注意的是,這個同志血淚史,所象徵的同志主體其實主要是「男同志」,而非女同志。女同志的抗爭史則在滾滾的男同志文化潮流中被湮沒了;電影、戲劇中,有許多豐富的男同志情慾題材,如:「孽子」、「藍宇」、「夜奔」、「喜宴」…等,雖然也有一些女同志的題材,如「自梳」、「美麗在唱歌」…等,但從整個電影的內容上來看,卻仍不免陷入異性戀與父權的景觀中,而形塑出女同的污名,像女同志都是因為感情受挫才轉向同性情慾。另外,相較於國外豐富的女同志紀錄片來說,台灣女同志的紀錄片竟是寥寥可數;同志書寫的部分,男同志的書寫也遠比女同志的書寫多且早,而形成相當豐富的資源,反觀女同志的書寫,就顯得稀薄與含蓄了。
造成這種狀態的形成,相當程度是因為,儘管隨著同志文化與空間的擴展、形塑,女同志們也努力的為自己爭取立足的空間點與發聲權力,然而,在異性戀霸權與父權的雙重作用下,台灣女同志相對來說是一個邊緣又邊緣的群體,不僅因為同志身分使其備受歧視,更因其為「女性」,而在社會地位中,相形弱勢。這樣的雙重弱勢,讓台灣女同志背負了比男同志更多的壓力,更加上,父權意識型態的內化與堅固,使得女同們在建構自身的主體性與情慾鬆放時,顯得較男同志更為退縮與壓抑。受制於此情形之下,台灣女同志在尋求破繭的過程中,常顯得能動性低,而不夠積極,也因而讓其在面對自身的性與認同時,得花許多氣力對抗內心的猶疑與外界的壓力才能有所突破。因此,如何解構、鬆解異性戀霸權與父權之雙全景敞視權力機制,在女同志建立與強化性與自我認同時佔據相當關鍵的一環。
第六章
結語
本文嘗試從權力的運作角度來看權力如何影響或壓制女同志自我身分認同與情慾之形成。由於女同志在性與自我認同的形構過程中,所遭遇的是一種微觀的權力運作影響。這種微觀的權力運作,是利用權力的微化,來深入受制者的行為之中,以便利用最省力簡便的行動方式來達到監控的效果,而邊沁的全景敞視建築即是這種理想的微觀權力機制模型,因此,在本文中便利用此模型來談關於台灣女同志的性與自我認同之問題。
女同志在建立自我身分認同與情慾的展放時,必須面臨的許多障礙與監控,而這些阻礙來自於「異性戀霸權」與「父權」兩個全景敞視模型的形塑與影響。異性戀霸權與父權利用意識型態的形構與知識的建構,並透過各種機制,如:教育、媒體再現、醫療…等,將這些意識型態與知識內化深入到社會機體中的每個人之行為思考裡,而形成其主流地位,進而達成完美的權力施展手段。
而在異性戀霸權與父權的雙全景機制的作用下,我們可以發現,女同志在經歷自我身分認同與情慾發展時,常常會將同性情慾解釋為姊妹情誼或者同性愛,加上污名化的同志標籤,因而讓女同志在建立自身的同志主體認同時,造成許多的不安與惶恐,甚至有逃避與自我污名化的情況發生,這對於女同志的同志主體認同的形成過程,造成變數與羈絆,而使得女同志在同志主體認同上顯得較為薄弱。另外,在雙重全景機制的交互作用下,女同志不僅對於自身的「同志主體」認同微弱,在面對同性情慾的過程裡,也常顯得無措與退縮。
此外,雖然在同志運動與女性主義的興起下,女同志得到的空間上的舒展與進步,然而,我們卻可以發現,除了集體空間所形成的集體認同感對女同志自我認同造成一定影響與助益外,台灣女同志的自我認同與情慾延展仍然有著相當大的壓抑情況,這是因為在集體認同之外,女同志所生存之空間的雙全景壓迫並未有徹底的解除與消失,因此在女同志個體的主體性建構裡,依然充斥著各種破壞性的能量,使得女同志之個體在免除集體的認同後,只存搖搖欲墜的認同薄膜。因此,要建立與強化女同志的性與自我認同,異性戀霸權與父權機制的解構將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參考資料
<中文書籍>
1.
台大女同性戀文化研究社,《我們是女同性戀》,碩人出版有限公司,1995。
2.
李銀河,《同性戀亞文化》,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3.
何春蕤編,《從酷兒空間到教育空間》,麥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2000。
4.
何春蕤編,《性/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上),元尊文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5.
杜修蘭,《逆女》,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6。
6.
周華山,《同志論》,香港同志研究社,1995。
7.
林芳玫,《女性與媒體再現-女性主義與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巨流圖書有限公司,1996。
8.
邱妙津,《蒙馬特遺書》,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
9.
邱妙津,《鱷魚手記》,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10.
紀大偉主編,《酷兒啟示錄-台灣當代Queer論述讀本》,元尊文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11.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
12.
梅家玲,《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麥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2000。
13.
莊慧秋等著,《中國人的同性戀》,張老師出版社,1991。
14.
莊慧秋主編,《揚起彩虹旗-我的同志運動經驗1990-2001》,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15.
張娟芬,《姊妹『戲』牆》,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
16.
張娟芬,《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17.
張小虹,《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
18.
張喬婷,《馴服與抵抗-十位校園女菁英拉子的情慾壓抑》,唐山出版社,2000。
19.
傅科,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
20.
梅奎爾,陳瑞麟譯,《傅科》,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
21.
鄭美里,《女兒圈-台灣女同志的性別、家庭與圈內文化》,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22.
鄭至慧、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23.
譚馨.史帕哥(Tamsin
Spargo),林文源譯,《傅科與酷兒理論》,貓頭鷹出版,2002。
24.
Gergoru M. Herek,江淑琳譯,《污名與性取向》,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2001。
<中文期刊、論文>
25.
洪雅琴,「女同性戀者的自我認同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心理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26.
陳麗如,「她們的故事:七個女同志的認同歷程」,屏東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1999。
27.
劉安真,「『女同志』性認同形成歷程與污名處理之分析研究」,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博士論文,2001。
28.
李元貞,「論台灣現代女詩人作品中『身體』與『情慾』想像」,中外文學,第二十八卷第四期,1999。
29.
郭明旭,「一個雙重的弔詭:媒體再現與同志污名」,南華大學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22期,2002。
30.
黃煜文,「試析傅柯的系譜作品-【規訓與懲罰】與【性意識史】」,西洋史研究通訊-歷史:理論與文化第二期,1999。
<報紙、新聞>
31.
姜炫煥,「遺書 沒有簽名
濟雅 只寫四行」,焦點新聞,聯合報,3版,1994年07月26日。
32.
藍凱誠,「女兒男友是女的,父親動手」,桃竹苗綜合新聞,聯合報,20版,
2003年01月25日。
<中文網路資料>
33.
陳思和,「鳳凰 鱷魚
吸血鬼-試論台灣文學創作中的幾個同性戀意象」,http://brahms.csie.ntu.edu.tw/~cs105sh21/chen.htm。
34.
楔子,「瀕臨惡崖」,同女心聲,La
Club–同女心路歷程,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Crete/6602/c-15.htm。
35.
鍾雲鵬,「父權意識的複製與傳承」,http://ms2.hyps.tp.edu.tw/~hy147/woman2.htm。
36.
「2,1」,http://www.labrys.org/21/press.htm。
<外文資料>
37.
Bentham J.(1995),The panopticon writing,NY:Verso.
38.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Y: Routledge.
39.
John Bowring(1995),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Vol 5,U.K.:Thoemmes
Press.
40.
Troiden, R. R. (1988). Gay and lesbian identity: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NY: General Hall, Inc.
41.
“The Panopticon of Jeremy Bentham”,
http://users.rcn.com/mackey/thesis/panpic.html。
42.
“Introduction:The
Panopticon”,
http://cartome.org/panopticon1.htm。
![]()
[1] 李銀河 《同性戀亞文化》今日中國出版社 1998 p13
[2] 張娟芬 《姊妹戲牆:女同志運動學》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8 p42
[3] 同註1 p5
[4] 周華山《同志論》 香港同志研究社 1995 p326
[5] 張小弘 《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6 p137
[6]
同註5
[7]劉安真 「『女同志』性認同形成立成語污名處理之分析研究」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博士論文 2000
[8] 同註7
[9] 傅柯著 劉北成、楊遠嬰譯 《規馴與懲罰-監獄的誕生》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8 p199
[10] 圖片資料來源:http://users.rcn.com/mackey/thesis/panpic.html
[11] 同註9 p200
[12] 同註9 p201
[13] 同註9 p201
[14] 同註9 p204
[15]
Gwendolyn Wright and Paul Rabinow著 陳志梧譯
「權力空間化-米歇.傅寇作品的討論」
《空間的文化型式與社會理論讀本》
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999 p378
[16] 黃煜文 《試析傅柯的系譜作品-【規訓與懲罰】與【性意識史】》 西洋史研究通訊-歷史:理論與文化第二期 1999
[17] 同註16
[18] 同註16
[19] 同註16
[20]梅奎爾著 陳瑞麟譯 《傅柯》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8 p119
[21] 同註9 p208
[22] 藍凱誠 「女兒男友是女的,父親動手」 桃竹苗綜合新聞 聯合報 20版 2003/01/25
[23] 郭明旭 「一個雙重的弔詭:媒體再現與同志污名」 南華大學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22期 2002
[24] 這是古代嚴懲婦女失貞的一種殘酷刑罰。它將「違反婦道」的女性裝進一個竹籠裡,然後綁上大石塊,接著將竹籠推進河裡或海裡,活活淹死。
[25]
鍾雲鵬
「父權意識的複製與傳承」
http://ms2.hyps.tp.edu.tw/~hy147/woman2.htm
[26]同註2 p85
[27] 鄭美里 《女兒圈-台灣女同志的性別、家庭與圈內生活》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7 p98
[28]
同註27
p98
[29] 陳麗如 「她們的故事:七個女同志的認同歷程」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9
[30] 同註29
[31] 同註27 p101
[32] 台大女同性戀文化研究社 《我們是女同性戀》 碩人出版有限公司 1995 p43
[33] 同註32 p45
[34] 同註32 p49
[35]
同註29
[36] 劉安真 「『女同志』性認同形成立成語污名處理之分析研究」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博士論文 2000
[37] 同註32 p14
[38] 同註36
[39]
姜炫煥
「遺書
沒有簽名
濟雅
只寫四行」焦點新聞
聯合報
3版
1994/07/26
[40] 楔子「瀕臨惡崖」 同女心聲 La Club–同女心路歷程 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Crete/6602/c-15.htm
[41]
同註2
p103
[42] 陳思和 「鳳凰 鱷魚 吸血鬼-試論台灣文學創作中的幾個同性戀意象」 http://brahms.csie.ntu.edu.tw/~cs105sh21/chen.htm
[43] 邱妙津 《蒙馬特遺書》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6 p11
[44] 同註2 p91
[45] 在朱天心的「春風蝴蝶之事」一文中,有著對女女關係的一段敘述:「她們是化學元素裡的惰元素與惰元素,不生變化,不發火光,不見詭異的顏色,我不曉得該如何稱呼她們,她們至為甜美,如同明迷清涼陽光下的春風蝴蝶。」這樣的女女關係的界定是一種不涉及肉體情慾的關係,是一種界乎柏拉圖式的精神情愛關係。因此,對於同女之間的無慾情愛組合,我們皆稱之為「春風蝴蝶」。
[46] 黃碧雲 「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引自張娟芬 《姊妹戲牆:女同志運動學》一書。
[47] 同註2 p92
[48] 陳斐雯 「蚤1」 《貓蚤扎》 1999。引自李元貞 「論台灣現代女詩人作品中『身體』與『情慾』的想像」一文。
[49] 同註2 p100
[50] 同註2 p100-101